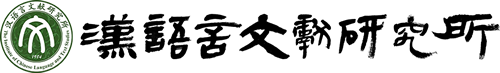摘要: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 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吸收以 “文化” 判别 “民族” 这一观点, 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如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制风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意识等) 来判别民族。除此主观标准之外, 实则不可忽视一个客观标准, 即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 如生理特征 (遗传特征)、 血缘关系 (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 等。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 “夷夏观” 的主体内容, 而 “以夏变夷” 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 “夷夏之辨” 的要义所在。
关于“种族/民族”与“文化”,陈寅恪曾经有过高明的论说。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对其“种族(民族)与文化”观又加以进一步阐述,“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1941年,在具体考证《魏书》中的江东民族时,陈寅恪又一次申述此论,“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
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陈寅恪“种族(民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民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民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惟因受论述对象和研究兴趣所限,陈寅恪的行文未能及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观。笔者的看法是:大体而言,以“文化”判别中古以来尤其是全球化以来的“种族(民族)”,本无可厚非;但是,以之观照先秦时期的古中国,则不可一概而论。因此,本人拟撰作此文以论述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史观。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传说时期”(五帝时代)和“历史时期”(夏商周三代),已有关于氏族(clan)、民族(ethnicity)、族团(ethnic group,一译“族群”)、种族(race)的传说和记载;而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遗址(遗迹)亦为数众多,并且构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惟因传说过于缥缈,记载过于简略,而考古研究又过于分歧(尤其是在将考古遗址与历史族群对应时),故本文将所考察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于先秦时期的周朝。当然,有时出于论述的需要和理解的方便,笔触亦将随文而及中古以降的时段乃至异域的西方。至于本文所考察、所论述的重点,则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判别“民族”的标准何在,二是“夷夏”之辨的要义何在。
一、从发生论/本根论而言,先天的生理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体质人类学的视角
◆ ◆ ◆ ◆
(一)生理特征与体质鉴定
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尤其是关于“种族”(race)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种族”属于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并且首先是生物学概念,它主要考虑的是生物学因素而非文化因素,“种族所涉及的是人类种群(human population)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它主要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它指的是“基于共同血缘的人们的地域群体,这种血缘关系表现在身体外表上有着许多类似的特征”,或“一群在他人看来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并在遗传上截然不同于他人的人”,亦即“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总之,即在体质上具有某些共同的遗传特征、共同的生物学基础(biological basis)的人群。本处所说的“在体质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包括肤色、眼色、发色和发型、身高、面型、头型、鼻型、血型、遗传性疾病等。
对于现代的人群和民族,可以通过观察、测量、检测等手段进行鉴别和鉴定,或者通过科学手段进行DNA分析。比如说,为了解决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有所谓“线粒体夏娃理论”(Mitochondrial Eve)的提出。对于中国古代的人群和民族,可以通过发掘所得的遗物(尤其是骨骼和牙齿)并有机结合历史学、文献学资料,进行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工作者已经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宝贵的成果。比如,潘其风研究了“中国古代人种和族属”“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种属问题”“先秦时期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再如,朱泓将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资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研究中国古代的人种问题;并积极吸收现代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最终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古人种学研究体系”。朱泓所做具体研究,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东北古代居民的种族成分研究”“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中原地区的古代种族”“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族”“僰人悬棺颅骨的人种学分析”“关于殷人与周人的体质类型比较”“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契丹人种初窥”“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靺鞨人种研究”“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DNA研究”等。
其实,对于体质人类学所揭示的不同人群(民族)具有不同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这一结论,中国古人是有所认识的。兹仅举三例,以为证据。
早在春秋时期,“博物君子”孔子对此已有认识。根据《国语·鲁语上》记载,“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所谓“骨焉,节专车”,即“骨一节,其长专车”。吴王遣使问孔子,孔子答以防风氏、僬侥氏事,防风氏“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即从骨骼和体格上区分人群(氏族)。早在2 500年前便有此认识,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降而至于西汉,《淮南子》的作者有着更为详细、更为丰富的认识。《淮南子·墬形训》说,东方之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南方之人“修形兑上,大口决龇”,西方之人“面末偻,修颈卬行”,北方之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中央之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隋人萧吉《五行大义·论诸人》的说法亦颇可参照,“东夷之人,其形细长,修眉长目,衣冠亦尚狭长。东海句丽之人,其冠高狭,加以鸟羽,象于木枝。长目者,目主肝,肝,木也,故细而长,皆象木也。南蛮之人,短小轻壑,高口少发,衣冠亦尚短轻。高口者,口人中,主心。心,火也,火炎上,故高;炎上,故少发也。西戎之人,深目高鼻,衣而无冠者。鼻主肺,肺,金也,故高;目,肝也,肝为木金之所制,故深;金主裁断,故发断无冠。北狄之人,高权被发衣长者。权主肾,肾,水也,故高权;被发者,象水流漫也;衣长,亦象水行也。中夏之人,容貌平整者,象土地和平也;其衣冠、车服备五色者,象土包含四行也”。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五行大义》在图式上出于“五行”整齐排列的需要,在思维上难免有不合实际的联想与比附(analogy),但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方之人“在体质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
中国古代典籍在记述王侯、大夫、贵族之时,尤其注重渊源和世系的叙述。其典型者,如《世本》《帝王世纪》以及《史记》之本纪、世家。所谓“渊源”(origin),即追踪本族(民族、氏族、家族)的来源(某位老祖父或老祖母);所谓“世系”(descent),即追记本族(民族、氏族、家族)与始祖的传承谱系。
不少学者指出,关于本族(民族、氏族、家族)的渊源和世系,实际上有“本来的历史”和“建构的历史”之别。具体而言,有的是“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如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有的是选择性的“历史记忆”甚至是事后的重构。
笔者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本处所说的“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特指并且专指具有真正的“共同的血缘关系”(common blood relationship)的民族(族群),亦即在DNA鉴定上可以认定的同一民族。惟有如此,方可视为具有“共同的祖先”(common ancestor)、“共同的世系”(common descent)、“共同的记忆”(shared memories)。
在西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下定义:“族群是这样一些群体,要么由于体貌特征或习俗相近,或者由于两者兼有,要么由于殖民和移民的记忆,从而对共同血统抱有主观信仰;这种信仰对于群体构建肯定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史密斯在给“民族”和“族群”下定义时,亦将“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的记忆”列为构成要素。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认定“族群”是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群,它一般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共同祖先的神话”即“共同的要素”之一。所谓“共同的神话和祖先”或“共同祖先的神话”,约略近乎本处所说“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世系”。
本处所说“共同的血缘关系”“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世系”,因为久远洪荒而不易找寻让人人都信服的证据。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一段文字(编号为176—178),确实是一则鲜活的例证。其原文如下: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去)夏”?欲去秦属是谓“(去)夏”。
“真臣邦君公有辠(罪),致耐辠(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
由以上简文可知,秦人已经以“夏”自居(自称),视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父母所生之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为“真”(他称)。至于如何判断是“夏子”还是非“夏子”,由简文可知,秦人注重的是血缘,并且尤其注重的是母方的血统。即母亲必须是秦人(“秦母”),其子方为“夏子”。
二、从生成论/过程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是判别民族的主观标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 ◆ ◆ ◆
(一)共同的语言文字
文化人类学认为,语言文字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习得)。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语言文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之一。因此,语言文字可以成为民族识别的依据之一。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所在,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一个民族的特性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总之,“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洪堡特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密切关系的特别强调,或许有些过分,但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在斯大林为“民族”所下定义中,“共同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之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论述的“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其四个民族特征的提出,是立足于他对欧洲民族的研究而得出的。也就是说,是就现代民族而言的。但以此反观中国古代民族,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的四个共同特征,还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密切关系,周朝时期的人士早已有清醒的认识。《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是从“族群”类别上对“五方之民”予以辨析,尤其强调“五方之民”语言的不同。诚因如此,故而“族群”(ethnic group)之间往往需要翻译方可交流。综合考察,《礼记·王制》的概括与记述是可靠的。春秋时期的戎子驹支,曾经坦言“诸戎”与“诸华”有诸多不同,而语言不同即其中之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六年)。而“诸戎”之间的语言也是互相不同的,“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战国策·燕策二》)。
在中原华夏族看来,蛮夷戎狄语言与华夏族语言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如此难懂,犹如“鸟语”。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讥讽操难懂的南方方言者为“南蛮舌之人”。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南方的少数民族被归入“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他们“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剔除其中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的成分,《孟子》和《后汉书》所反映的历史(民族和语言)还是很客观的。
非常可贵的是,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不但认识到可以通过语言判别民族(不同民族有不同语言),而且认识到语言与民族的对应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即语言的改变并不影响族群身份的认同。《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也就是说,楚人和戎人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因为语言的改变而发生变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近代。从近代许多国家的族群发展状况来看,随着人口迁移和族群之间混居与广泛交流,有一些族群虽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改用其他族群的语言,但这些族群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中国的回族、满族已经通用汉语,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已经使用当地语言,但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
(二)共同的社会生活
本处所说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与斯大林所说的“共同经济生活”有交叉、有重合,特指衣、食、住、行等。兹略举数例,以为证据。
《尚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孔传:“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发左衽之人,无不皆恃赖三君之德。”“被发左衽”是“四夷”的装束,与“华夏”的“束发右衽”判然有别。诚因如此,故孔子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叹(《论语·宪问》)。“四夷”与“华夏”在衣、食上的不同,四夷之人其实有着自觉的认识。《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戎子驹支语:“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礼记·王制》对“中国”“四夷”之别的概括颇为全面,“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的概括亦相当全面,“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
(三)共同的礼制风俗
本处所说的“礼制风俗”,即古书所云“礼俗”。“礼”(礼制)和“俗”(风俗)在中国不但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至传说时期的尧舜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而且关系密切(“礼”渊源于“俗”而又高于“俗”);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人所说的“文化”,即“文治教化”,亦即“为文所化”。其中,礼是“文化”的大宗。以“文化”判别“民族”,实即以“礼俗”判别“民族”。
在中国古人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之所以为“中华”,并非仅仅是因为居于“天下之中”,更多的是因为有礼乐之隆、仁义之施、文化之美。对“中国”与“中华”的这一共同的认识,不但见诸周朝文献,亦广泛见于后世典籍。《战国策·赵策二》:“公子成再拜曰:‘……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庄子·外篇·田子方》:“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唐律疏议》卷四《名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远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石介《中国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缞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至于近代,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
正因如此,在整个周朝时期,礼制成为判别夷夏的极其重要的标准。比如,《左传》定公十年:“孔丘以公退,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正义:“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莱是东夷,其地又远,‘裔不谋夏’,言诸夏近而莱地远;‘夷不乱华’,言莱是夷而鲁是华。”(《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再如,杞国封君为大禹后裔,其血统属于华夏系统,其礼制亦属于华夏文化系统;但因杞国国君在春秋时期使用“夷礼”,故而被时人视为夷,国君亦被贬称为“杞子”。《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又如,秦国祖先虽然是“帝颛顼之苗裔”(《史记·秦本纪》),但在东周之时仍然被视为夷狄。其原因有二:一是地理因素,“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二是礼俗因素,“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
(四)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英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史密斯的行文表述中,“族群”与“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是相互对应的,体现的都是族群的感情心理因素,而这也是“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认定“族群”是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群,它一般具有“共享的历史记忆”等要素。中外各民族的史诗、各族群的谱牒,所展示、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亦即史密斯所说“共享‘黄金时代’的记忆”。
所谓“史诗”(epic poetry),是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的叙事长诗,具有民族历史的性质。世界著名的史诗,如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等,以及古中国的《格萨尔王传》(藏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等。这种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共同的”(common),也是“共享的”(shared)。
所谓“谱牒”(genealogy),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是“记载一家一族的历史”(夏衍《方志学与家谱学》)。《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唐人刘知几曾经举例说明,“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録》,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史通·书志》)。《国语·楚语上》记录了楚国大夫申叔时教导太子的内容,其一即“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所谓“世”,即“谓先王之世系也”(韦昭注)。《国语·楚语上》的记载和韦昭的注是可信的,因为它们合乎上古中国的传统,并且为出土文献所印证。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记述的是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微氏家族的发展历史(《殷周金文集成》10175)。史墙盘如此而为,合乎上古中国的传统,即《礼记·祭统》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墨子·天志中》所说“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其目的在于使整个家族(民族)保持“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黄金时代’的记忆”。
(五)共同的民族意识
本处所说“共同的民族意识”,即“民族认同意识”(nat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有时也称为“族群认同”(ethnical identity)。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图沃德(Melville Y.Stewart)强调,“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中国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得以确立的、对于主体所在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费孝通一再强调,“民族认同意识”是多层次性的,而“民族认同意识”可以作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今人指出,“华夏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是自夏代以来就客观存在的。“华夏民族意识”是在夏商周时期逐渐产生、逐渐形成的,最终形成于春秋时期。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认同”,大概经历了西周早期周人对夏的“血缘认同”、春秋时期诸族群主要是对华夏的“文化认同”、战国时期周属族群对华夏的“区域认同”等三个大的阶段。东周之时,华夏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是极其强烈、极其鲜明的,时人普遍认为,华夏民族(中国)与蛮夷戎狄(四夷)是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这种民族意识的经典表述,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国语·楚语上》所说“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亦颇为典型。先秦时期形成的这种“民族认同意识”,一直影响到后世。比如,《晋书·江统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套用美国社会科学家William Graham Sumner Folkways一书的说法,“我之族类”即“in-group”,“非我族类”即“out-group”。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民族认同意识”,实际上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分析。在先秦时期(尤其是在东周时期),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血统而言本来属于华夏族的诸侯,因熏染了蛮夷夷狄的习俗,故又以蛮夷、夷狄自居。其典型例证,有燕国、吴国、越国、楚国等。
1. 燕国
先秦时期,曾经存在过两个燕国,一个是姞姓燕国,一个是姬姓燕国。本处所说的燕国,指的是姬姓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与鲁国一样,燕国也是“以元子就封”。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宫。”《史记·燕召公世家》司马贞索隐:“(燕)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司马迁、郑玄、司马贞之说,业已为出土的太保罍(克罍)、太保方盉(克盉)铭文所证实。因此,“召公封燕”一说不容置疑。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历史上的燕国国君曾经竟然以“蛮夷”自居,而燕国勇士秦武阳(秦开之孙)也被人称为“北蛮夷之鄙人”。《战国策·燕策一》:“燕王曰:‘寡人蛮夷辟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求正,谋不足以决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请奉社稷西面而事秦。’”(参见《史记·张仪列传》)《战国策·燕策三》:“荆轲顾笑(秦)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
2. 吴国和越国
就吴国和越国之王室而言,他们在血缘关系、祖先传说、历史记忆上与华夏民族(禹)、周朝王室(太王)有关系,可以划入华夏族系统;但其行为、风俗、心理已与中原华夏族截然有别,故被中原诸侯轻蔑地视为“蛮夷”“夷狄”。与此“他者”的眼光相对,吴、越国君亦自我认同为“蛮夷”“夷狄”。
吴国的始祖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属于西周王室系统。太伯及其弟仲雍入乡随俗而“文身断发”,这是吴国被他人视为“夷狄”的重要原因;后来的吴国国君,亦因此而以“蛮夷”“夷蛮”自居。《越绝书·越绝吴内传》:“吴何以称人乎?夷狄之也……吴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称人,贱之也。”这是吴国被他人视为“夷狄”。《晏子春秋·外篇·吴王问齐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对以岂能以道食人》:“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请私而无为罪。’”(参看《说苑·奉使》)此处以“蛮夷之乡”与“君子之行”对举,我们可以体会这样一层意蕴:吴王虽未明确以“蛮夷”自居,但实则认同“蛮夷”之风尚与习俗。《晏子春秋》《说苑》和《越绝书》所隐含的这一意蕴,对照《史记》《吴越春秋》的记述便昭然若揭。《史记·鲁周公世家》:“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吴王寿梦、夫差在“民族认同意识”上的认识是自觉而清楚的:因为入乡随俗而“文身”“椎髻”,在礼制风俗上与中原华夏族已然有别,故遂以“蛮夷”“夷蛮”自居。
按照正史的记载,越国的祖先可以与大禹挂钩。《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与吴国如出一辙的是,越国也被他人视为“夷狄”,而越国国君亦以“夷蛮”自居。《韩诗外传》卷八:“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者。’”由此可见,越王勾践时期的楚国已经以华夏族自居,反而视越国为夷狄。《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子贡东见越王,越王闻之,除道郊迎至县,身御子贡至舍而问曰:‘此乃僻陋之邦,蛮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于此?’”
3.楚国
楚国芈姓,出自“五帝”之一的颛顼,与华夏族的黄帝、炎帝有血缘关系。《楚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按照出土文献的记载(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葛陵楚简、安大简等),楚国出自祝融。在楚简中,祝融与老童、穴(鬻)酓(熊)并列,被称为“三楚先”(即《离骚》所说“三后”),是楚人祭祀的三位先祖。而祝融亦属颛顼之后。《吕氏春秋·孟夏纪·孟夏》:“其神祝融。”高诱注:“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对楚国早期世系的记载是极为清晰的,即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连(穴熊)。安大简的出土表明,“老童、祝融、穴(鬻)熊”之为“三楚先”是确定无疑的史实;安大简楚史与其他楚简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是一致的,是“战国时期楚人业已形成的统一看法”;因此,“安大简楚史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官修史书”。但是,楚国国君后来竟然以“蛮夷”自居(“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非常有意思的是,连“天子”周惠王亦将楚国归入“南方夷越”之列。《史记·楚世家》:“(楚)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燕国、吴国、越国、楚国的国君之所以以“蛮夷”“夷蛮”自居,其重要原因便是因为他们熏染、接受了蛮夷戎狄的文化(礼制风俗、社会生活等)。这一现象,从反面证明上文所说第二点(“共同的社会生活”)、第三点(“共同的礼制风俗”)的可信性。格罗斯比说,“人承认自己是民族一员,只是对自己身份的多种表述之一。形象地说,这只是多层自我意识的一层。”格罗斯比所云,与本处所说近似。史密斯亦尝指出,“民族的认同,这可能是最难以捉摸的”。质言之,“民族认同意识”固然可以作为判别民族的主要标准之一,但确实不可一概而论。最为经典的反证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孟子·离娄下》,参看《韩诗外传》卷五),但舜和周文王都被尊为华夏族的“圣人”。
三、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流: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 ◆ ◆ ◆
本处所说这一点,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说,田继周在写作《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时,便特意揭示这一层意思。田继周说,“周朝民族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上”。随后,他从以下两个层面对此进行论述。(1)《礼记·明堂位》记载了“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三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以及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等人所站立的位置是很讲究的,公侯伯子男等站立于门内,而蛮夷戎狄则站立于门外,“明堂位的排列,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的歧视观点”。(2)在周朝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把戎狄比作“豺狼”“禽兽”的记载。《左传》闵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管仲语)《左传》襄公四年:“戎,禽兽也。”《国语·周语中》:“狄,豺狼之德也。”(富辰语)《国语·周语中》:“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周定王语)“周朝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压迫的政策”,周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时,又往往结合具体情况,采用武力征伐和‘文教’安抚两种手法”。
其实,除以上两点之外,至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点(第三点),即东周时期民族不平等思想、民族歧视观念的形成和确定,儒家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后人的概括,孔子之作《春秋》,恪守的法则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在孔子的心目中,华夏民族的文化无疑是高于蛮夷戎狄的,故而明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降而至于孟子,则进一步提出要“以夏变夷”,反对“以夷变夏”,“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套用《穀梁传》襄公十年的说法,即“不以中国从夷狄也”,而其大义在“存中国也”。孔子、孟子与《穀梁传》的这些话语,是“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的经典表述。它们“一分为三”,经典地揭示了古中国“夷夏/华夷”观的“三部曲”:“夷夏有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夏变夷”是主流的价值取向,而“存中国”则是终极的追求与目标。
儒家这种“夷夏有别”、“以夏变夷”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书·萧望之传》:“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这是孔子“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翻版。宋人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明人邱濬接着说:“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大学衍义补》卷七五)可见,后人所说的“华夏中心主义”(或“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实际上可以溯源于儒家。而近代以来流行的保国、保种、保教思想与主张,实际上亦可以溯源于古中国的“夷夏/华夷”观。
结语
◆ ◆ ◆ ◆
结合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审视中国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发现:
其一,判别“民族”的标准实则可以一分为二:(1)基于先天的生理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如生理特征(遗传特征)、血缘关系(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等。尤其是在民族形成的早期阶段(比如夏商周三代或东周时期),这种民族鉴别更为行之有效。(2)随着民族的频繁交往尤其是民族的日益融合,后天的文化因素日渐成为判别民族的主观标准,亦即以“文化”判别“民族”。这些主观标准,包括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礼制风俗、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意识等。在“民族认同意识”上,需要审慎对待,不可一概而论。
其二,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夷夏观”的主体内容,而“以夏变夷”则是其主流导向,这是周朝“夷夏之辨”的要义所在。东周时期民族不平等思想、民族歧视观念的形成和确定,儒家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文章原载于《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关于作者
彭华,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著有《燕国八百年》《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民国巴蜀学术研究》《印川集:蜀学散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