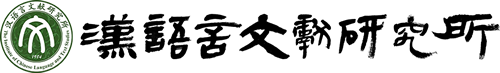安大簡《詩經》《秦風》之後、《甬(鄘)風》之前有“矦”,整理者指出,《矦》“內容為《毛詩·魏風》中的《汾沮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鼠》《十畝之間》六篇”,“第八十三號簡中部有‘矦六’二字,應即指此六篇”。“簡本‘矦’作為一國之風名,未曾見文獻記載,黃德寬疑即‘王風’”。“朱熹《詩集傳》:‘然其王號也,故不曰周而曰王。’戰國楚簡抄本則直接稱之以‘矦’,蓋有‘貶之’之意。《矦》所屬《魏》風六篇,疑為抄手誤置所致”。
應該說,這樣的推斷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安大簡《詩經》的國風之編排實在有點混亂。《矦》下是《毛詩》之《魏》風六篇,而安大《詩經》又自有《魏風》,第“百十七”號簡末有“魏九 葛婁(屨)”四字。整理者說,“魏九 葛婁(屨)”,指《魏》共九篇(實有十篇)。但是,“除首篇《葛屨》屬《毛詩·魏風》外,其餘九篇皆為《毛詩·唐風》內容”。所以,安大《詩經》之《魏風》,名不副實,名存實無。
不過,黃德寬之說也有疑點。主要是,如果“矦”是《毛詩·王風》,為何內容與《王風》毫不相干?經反復審視研究,我認為所謂的“矦”,應當就是《魏風》。理由如下。:
其一,《矦》下數篇皆《魏風》內容。《毛詩·魏風》共有七篇,即安大簡《詩經》第“百十七”號簡所記“魏九 葛婁(屨)”及《矦》所轄《汾沮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鼠》《十畝之間》六篇。也就是說,安大簡《詩經》,除了“魏九”之“九”計數不實外,收納了《毛詩》的全部《魏風》。其二,《魏風》為何在安大簡《詩經》裡稱“矦”呢?我們認為可能抄寫者是魏國人。
戰國時魏國國君稱“侯”,最著名者是魏文侯與魏武侯,其在位正當戰國早中期。《史記》記,文侯在位三十八年,《索隱》云:“三十八年卒。《紀年》云五十年卒。”武侯在位十六年。《索隱》云:“按《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用《紀年》說,排文侯五十年,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排武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95年至370年。傳魏文侯曾受教於孔子弟子卜子夏。《史記·魏世家》記:“文侯受子夏經藝。”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關於子夏為魏文侯師,可參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二·三八《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考》、四〇《魏文侯禮賢考》,上海書店,1992年。)衆所周知,子夏與《詩經》關係密切,《仲尼弟子列傳》記,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是對子夏學《詩》的極大肯定。傳《詩序》即子夏所為。《關雎序》孔穎達疏云:“小序是子夏作,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269頁,1980年。)如此看來,安大簡《詩經·魏風》有可能與魏文侯有關。這裡所謂的“有關”,是假設安大簡《詩經》的祖本為魏人所抄寫,因此其對本國國風的稱呼就直接寫作“矦(侯)”,即魏文侯(或武侯)。這一假設如果能夠成立,則我們不僅可以判定該《詩經》抄寫者的國別,也大致可能確定抄寫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前言》說:“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對竹簡、竹笥殘片和漆片等三種樣品進行了年代檢測,測定其年代距今約二千二百八十年左右。其後,國家文物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進行了化學檢測分析,也確認這批竹簡時代為戰國早中期。”這樣,安大簡的年代,我們所分析的該《詩經》之祖本的抄寫時間應在魏文侯(或武侯)的時期恰能吻合。世間有這樣巧合的事情嗎?安大簡本《詩經》先經魏人抄寫初定型,後來想必又輾轉經歷多次傳抄講授,才成為我們今天見到的楚文字簡本。不論是魏人嫻習楚字,抑或是楚人抄寫魏本,總之都留下了經典發展流佈的匆匆的腳步的印跡。
作者简介:
胡平生,1945年生于上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吉林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62年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1978年入同校同专业为古文字研究生,师从裘锡圭先生。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与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论著(含合著与集体项目)有:《孝经译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阜阳汉简诗经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