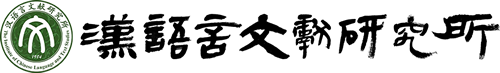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1.05-11.07).pdf
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1.05-11.07).pdf
11月5日研讀《干旄》一詩,主要討論了對“良馬五之”的理解。
蕭聖中首先指出,在其2005年博士論文《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中論及《干旄》中“良馬五之”應當釋作駕五匹馬,而不是古注所言五根馭索。漢代畫像磚、九連墩弩機上有駕五馬圖可證。董珊認為:“上言‘絲組’,下言‘馬五’,五應讀為配合意義的伍。楊家村銅器器主名逑,字五父,逑、五(伍)詞義相近。”對此,蕭聖中指出上下文是四馬、五馬、六馬,孔廣森早有觀點認為“良馬五之”是馬數而非轡數,不過此觀點在其文中漏引。
11月6日主要研讀了《葛履》一詩,涉及到文字學、音韻學、文獻學三個方面的問題。
文字學方面,孟蓬生提到“摻(纖)”字(安大簡作
![]() )與“
)與“
 ”字(安大簡作
”字(安大簡作
![]() )字形上的問題。認為釋作“摻(纖)”的字嚴格隸定的話,兩個蟲之間應該有一“○”或“囗”的構件;“
)字形上的問題。認為釋作“摻(纖)”的字嚴格隸定的話,兩個蟲之間應該有一“○”或“囗”的構件;“
 ”字跟以前从止从琮的那個字形應該有區別。
”字跟以前从止从琮的那個字形應該有區別。
音韻學方面,孟蓬生補充道:“影母(宛)與明母(俛)相通,可以與見母(教)與明母(芼)相通互相參證。這對於影母為塞音(而不是零聲母)的構擬或許是有利的證據。”
文獻學方面,呂珍玉首先提出:“安大簡比毛詩多出‘可以自適’一句,這句與上文‘可以履霜’‘可以縫裳’問的對象不同,前者是問被刺的享受者何以能自適,後者是同情縫裳者怎堪辛勞。”并由此提出兩點疑問:①“可以自適”在“維是褊心”前,是因她器度狹小,是以寫此詩為刺?②前已言好人“宛然左避”,後又問“何以自適”在語義上是否重複?
11月7日研讀《蟋蟀》一詩,主要圍繞安大簡本“良士浮浮”與“猷(猶)思其憂”兩處異文展開討論。
一、“良士浮浮”與“良士休休”
呂珍玉認為,安大簡整理者認為毛詩本“良士休休”“役車其休”重用“休”字,這點上安大簡本“良士浮浮”較好;整理者引《楚辭》訓“浮浮”為“行貌”,於詩意解釋還不錯。她接著說道:《詩經》中重言聲音構詞豐富、多義,如“雨雪浮浮”“烝之浮浮”,安大簡本“良士浮浮”又增一例。對此,孟蓬生指出:“‘休休’與‘浮浮’都是記音,因此似乎不存在重複和優劣的問題。《說文·桼部》:‘䰍,桼也。从桼,髟聲。’大徐本“許尤切”。《玉篇·髟部》:‘髹,赤黑漆也。髤,同髹。’休之於浮,猶髹之於䰍也。髹,實際上也可以看成雙聲符字,髟、休皆聲。”
譚樊馬克由孟蓬生之例提到“飍(香幽切)”與“驫”、“猋”實為同源字,飍同時讀幫母、曉母和並母,飍對應了髹的兩個聲符的兩個聲韻地位,也對應休、浮兩個異文的聲韻地位。孟蓬生指出:“其實都是‘風’的派生詞,侵幽對轉而已。”譚樊馬克表示贊同,且說明王育弘已從高棉語的角度找到對應詞族。
蕭旭補充了兩則材料:《廣雅》:“䞯,行也。”《說文》:“𠓗,疾也。”䞯重言就是行貌,浮浮就是往來疾行貌。又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篇》《廣韻》皆曰:‘急疾也,今作䞯。’《少儀》曰:‘毋拔來,毋報往。’注云:‘報讀為赴疾之赴。’按赴、䞯皆即𠓗字,今字𠓗、䞯皆廢矣。”他認為:“風的語源義是盤旋,與三兔合文的字(記錄者按:指𠓗)不同源。”孟蓬生提醒:“要求同存異,語源學本來就是主觀性較強的學科。”
劉洪濤提出:“三馬、三兔、三犬讀音近,大概就是後來的‘跑’,曾良先生講過,屬於俗文字的範疇了,古文字三‘兔’音‘宛’。三‘風’这个字当是根據‘飆’造的俗字。”又認為《蟋蟀》詩旨是講及時行樂,同時勸勉不要荒怠,要勤勉公事,對於“浮浮”“休休”等重音詞,當訓為疾行的引申義‘勤勉’。
對於譚樊馬克提到外族語言的證據,蕭旭表示懷疑:“汉藏同源都是假说,其他的更远。”對此孟蓬生指出:“漢藏語是否同源,只有比較過後才能下結論。因此不管漢藏語是否同源,比較研究都是積極的和值得肯定的。”
二、“猷(猶)思其憂”與“職思其憂”
“職思其憂”之“職”如何訓釋,自清代就有討論。毛詩本作“職思其憂”,安大簡異文作“猷(猶)思其憂”,孟蓬生借助新材料對“職”和“猷(猶)”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他同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丁聲樹先生《詩經“式”字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冊)、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裡的“式”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人的意見,認為“式”和“職”是表示勸令和希冀的語氣詞。《陟岵》“猶來無止”“猶來無棄”“猶來無死”之“猶”,跟“式”“職”等字一樣,是表示祈使語氣(勸令或希冀之詞)的副詞。安大簡《詩經》作“允”,與“式”“猶”古音相通。式、允、猶三者的關係,跟弋、鐏(錞鐓)、尗三者的關係和“玳瑁”“頓牟(簪)(尹灣二號漢墓木牘,參看馬怡《尹灣漢墓遣策札記》)”“蝳蝐”三者的關係大致平行。
蕭旭對此補充了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材料各一則:青島土山屯墓群M147木牘《堂邑令劉君衣物名》:“頓茅橫蠶(簪)二。”馬宗霍《論衡校讀箋識》:“‘頓牟’蓋‘瑇瑁’也,雙聲字。‘突牟’即‘頓牟’也。‘琥珀’與‘瑇瑁’要為二物,當並存以俟考。”
蕭旭認為“職”今語義約為當,表示應當如何,是一個命令副詞。孟蓬生指出:“對於古書中的虛詞,還是用描寫法比較好些,前人多用訓詁法,常常容易誤會。”並且說明現代漢語中實際上沒有完全相當的虛詞。
劉洪濤援引了沈培《西周金文中的“䌛”和〈尚书〉中的“迪”》一文的觀點,認為“猶”是沈培所說的“迪”,而不是“職”。對此孟蓬生認為可以存異:“沈培先生把金文中的‘繇唯’跟《尚書》中的‘迪惟’認同,我是很贊成的。但我不同意把《詩經》‘猶思其憂’‘猶來無已’等句子中的‘猶’跟金文或《尚書》‘繇’或‘猷’認同。”孟蓬生提出以下三點理由:
(一)“繇唯(迪惟)”之“繇(迪)”跟“猶來無已”之“猶”語法分佈不同。“繇唯(迪惟)”放在名詞主語之前,“猶思其憂”“猶來無已”中“猶”字直接用在動詞前。
(二)“猶來無已”之“猶”跟“猷告”“猷大告”之“猷”語法分佈和功能不同。“猷大誥爾多邦”“猷誥爾四國多方”等是陳述句,而“猶思其憂”“猶來無已”等是祈使句。用在陳述句和祈使句的這兩個字的語法功能至少應該假定是不同的。
(三)“職思其憂”的“職”和“猶思其憂”的“猶”的用法應該認同。之職和幽覺關係上古音較近,所以兩者之間應該看成假借關係。
劉洪濤對孟蓬生補充的三點理由表示贊同。
執筆:黃春蕾
審覈: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