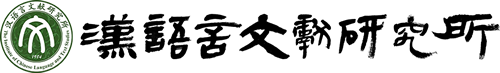讀《睡虎地秦墓竹簡》札記一則
党翊翀
(華中師範大學法學院)
《秦律雜抄》簡26“公車司馬獵律”有簡文如下:
·射虎車二乘爲曹。虎未越泛蘚,從之,虎環(還),貲一甲。虎失(佚),不得,車貲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貲一甲。·豹旞(遂),不得,貲一盾。·公車司馬獵律[1]
“徒”,整理小組引《說文·辵部》:“步行也”,將“徒出射之”譯作“出車徒步射虎”。[2]《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簡牘秦律分類輯析》《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集釋》等譯文皆沿用此說。[3]
今按:法律規則通常具有一定的邏輯結構,一般要完整包含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這三種要素。法律規則是法律條文的內容,法律條文是法律規則的形式,但法律規則與法律條文並不絕對是一一對應關係。《公車司馬獵律》由五條法律條文構成,第一條屬於規定法律概念和法律技術的非規範性條文,其附屬於餘下四條規定法律規則的規範性條文適用。四條規範性條文都僅規定了法律規則的兩個要素,即假定條件和法律後果。

“虎未越泛蘚,從之,虎環(還)”“虎失(佚),不得”“虎欲犯,徒出射之”“豹旞(遂),不得”乃假定條件,明確了適用該條法律規則的特定條件;“貲一甲”“車貲一甲”“貲一盾”等法律後果,是法律規則中規定行為主體在作出特定行為時應承擔相應後果的部分。“法律規則的確定性程度較高,這個確定性包括它的內容相對明確與恆定,它的效力也較為清楚明確”,[4]“虎欲犯,徒出射之”一句,若按通說譯作“虎要進犯,出車徒步射虎”,則僅指出了適用該條法律規則的時空情境,卻未規定假定條件中的特定行為主體,影響了法律規則的確定性。[5]所以,“徒”當釋為指代某一特定行為主體的名詞,而非動詞“徒步”。
有學者認識到本條律文的“徒”當作名詞解,但認為“‘徒’所從事的工作為‘射虎’,其身份很有可能是刑徒,‘徒’的指代對象從服役的農民向為官府服役的刑徒轉化。”[6]從“徒”之字義流變看,吳榮曾先生指出:“徒在春秋時主要是指服徭役的農民,戰國時刑徒開始分擔起原先由農民所承擔的徭役,故他們也被稱之為徒。由於刑徒具有不自由的身份,並當作奴隸來使用,故當時人把徒和隸連在一起。”[7]杜正勝則認為,封建時代“徒”的身份是自由民,卽司徒所掌握的平民大眾,也是軍隊的大多數成員。罪隸名作“徒”,係漢朝以下的事,直到秦代“徒”“隸”之間劃分依然非常清楚,徒是自由民,隸是罪犯。二者混淆發生於西漢初期,或為勞役刑普及,罪隸多擔任古代徒的役事之故。[8]諸家雖在具體表述上有所差異,但對“徒”之字義演變趨勢的認識基本一致。這一點沒有疑問。然釋本條律文的“徒”為“刑徒”的省稱,於事理似有未安之處,仍可商榷。
“公車司馬”,整理者注“朝廷的一種衛隊”,並引《漢書·百官公卿表》為證。[9]公車司馬衛隊參加田獵活動時,有專門的法規規定其捕獵程式以及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措施,本條律文規定的就是射虎車隊的編成、獵虎規制與罰則,是公車司馬衛隊參加田獵的法律規定。[10]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簡449列有公車司馬一職,其與太倉治粟、太倉、中廄、未央廄、外樂等同屬中央九卿之屬官,秩各八百石。[11]《漢書》顏師古注引《漢官儀》曰:“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12]可見公車司馬具有秩級,這一機構承擔警衛宮門、巡視宮廷等重要職能。如此舉足輕重之任務,朝廷又如何會讓有罪的刑徒執行?故此說不確。
先秦時期,田獵與軍戰並無二異,“戰爭最初出現於原始公社制瓦解時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獵工具,戰爭方式也和集體圍獵相同。等到國家產生,軍隊成為國家統治工具,進攻成為掠奪手段,軍隊組織有進一步加強,戰爭方式有進一步發展,但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戰爭武器還和田獵工具相同,戰爭方式還和田獵方式相同。”[13]出動禁軍衛隊進行田獵活動,軍事訓練與演習的性質可見一斑。另外,結合《秦律雜抄》秦人行大蒐禮的記載及龍崗秦簡所見《禁苑律》,亦可發現秦人之田獵活動除了軍事訓練與演習的特征,還具有軍禮的性質。[14]《周禮·夏官》對這種活動有詳細記載: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躁。徒乃弊,致禽馌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15]
從上述記載看,大蒐禮的主要訓練活動都是圍繞車徒展開的,說明徒卒作為一個兵種此時仍依附於戰車,這與先秦時期車戰興盛的時代背景相適應。先秦之戰車,每乘配備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排列。除車上的三名甲士,還配屬一定數量的步兵,成為“徒”或“卒”。在戰鬥中,甲士與步兵相互配合,戰車衝鋒在前,徒兵屏蔽於兩側,伺機發起進攻。
綜上言之,《公車司馬獵律》中的“徒”當釋為名詞“步兵”,所謂“徒出射之”,意卽步兵出車射虎。此句當譯作:虎要進犯,步卒出車射虎而沒有獵獲的,罰一甲。
[1]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頁
[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頁。
[3] 劉海年等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 第一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27頁;孫銘編著:《簡牘秦律分類輯析》,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頁;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基礎史料研讀會:《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集釋(六):秦律雜抄》,載徐世虹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頁。
[4]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頁。
[5] 若以“射虎車”為該假定條件的行為主體,此句可補全為“虎欲犯,(射虎車)徒出射之”,譯作“虎要進犯,(射虎車)出車徒步射虎”,於文理不通,顯然有誤。
[6] 李亞光:《戰國秦及漢初的“徒隸”與農業》,載《中國農史》2018年第3期。
[7] 吳榮曾:《胥靡試探——論戰國時的刑徒制》,原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收入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56頁。
[8]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2-306頁。
[9]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頁。
[10] 栗勁:《秦律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頁。
[11]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頁。
[12] [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729頁。
[13] 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3頁。
[14] 參見曹旅寧:《從秦簡公車司馬獵律看秦律的歷史淵源》,收入氏著《秦漢魏晉法制探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頁;朱瀟:《“田獵”與“校獵”:秦漢官方狩獵活動的性質變化》,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15]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汪少華整理,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825-28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