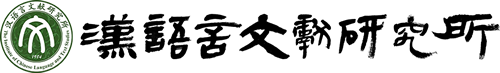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1.02-11.03).pdf
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1.02-11.03).pdf
11月2日的討論由《君子偕老》一首展開,主要涉及音韻學。討論以下兩個問題:一是與“也”聲相關的支、歌關係問題;二是“埶樂”與“紲袢”的關係問題。
一、與“也”聲相關的支、歌關係問題
安大簡“不
![]()
![]() 也”,《毛詩》作“不屑髢也”。
也”,《毛詩》作“不屑髢也”。
整理者將“髢”歸入歌部,王寧對讀安大簡與《毛詩》的《君子偕老》第二章時,懷疑《毛詩》“髢”所从的“也”是“只”字之誤。劉洪濤指出:“其實‘也’屬支部,根據先秦秦漢古文字資料,凡是讀音屬於歌部的从‘也’之字都是‘它’字的訛变。从‘也’字的本義以及韻文、假借、讀若等資料來看,上古音‘也’字應該歸入支部。”(詳見劉洪濤:《上古音“也”字歸部簡論》,《中國語言學》第三輯。)孟蓬生隨及補充:“李家浩先生指出‘只’‘也’爲一字分化。”(李家浩:《釋老簋銘文中的“
![]() ”字——兼談“只”字的來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譚樊馬克認爲:“支歌之間很多字還能商榷,似乎兩歸都行。如‘兮’就有支歌兩種觀點。”
”字——兼談“只”字的來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譚樊馬克認爲:“支歌之間很多字還能商榷,似乎兩歸都行。如‘兮’就有支歌兩種觀點。”
薛培武認為:“簡文‘
![]() ’,如果讀若‘殺’,還能勉強入韻。歌部的那種‘衰’,跟‘殺’很可能同源,同訓‘差’。”譚樊馬克指出:“‘衰’也可以是歌部。‘衰’‘危’兩個聲符在歌、微之間。”
’,如果讀若‘殺’,還能勉強入韻。歌部的那種‘衰’,跟‘殺’很可能同源,同訓‘差’。”譚樊馬克指出:“‘衰’也可以是歌部。‘衰’‘危’兩個聲符在歌、微之間。”
孟蓬生指出:“考慮到語料的非同質性(即非一時一地之材料),古音歸部應該有一定的靈活性,不必過于執著。即以支(段氏第十六部)、歌(段氏第十七部)兩部爲例,段玉裁既主張第十七部(歌部)獨用,又有‘第十七部與第十六部同入’說:‘第十七部與第十六部合韻最近,其入音同第十六部。’還說:‘古十七部之字多轉入於支韻中。’他在《說文解字注》中也常常用某兩部之間的說法,如‘也’字下注:‘故其字在十六十七部之閒也。’‘𪓿’字下注:‘古音在十六部十七部之閒。’‘𨻌’字下注:‘古音在十六、十七部之閒。’是其例。如果說支和歌上古絕對不能相通,中古的支韻怎麼會有來自上古歌部的字呢?現在許多爭論實際上是盲人摸象,各執一詞。”接著他舉出了《詩經·小雅·斯干》相關韻例: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他指出:“這兩章除了第一句外,是兩個三疊句,句句入韻。有人懷疑‘裼’字不入韻是不合適的。《春秋繁露·五地》:‘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釋名·釋地》:‘地,……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白虎通義·天地》:‘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詩經·小雅·斯干》之‘裼’字,陸德明《經典釋文》:‘“裼”,《韓詩》作“𧝐”。’綜合以上材料,支歌兩部至晚從春秋以前就已經開始合韻了。”
王弘治就支、歌歸部問題提出:“中古支韻中諧聲屬歌的字,很多是規則變化,一等轉入歌,三等轉入支,具有一定語音條件,不足爲怪。但部分字,比如‘髢’讀齊韻的現象,因爲四等屬於高元音來的,不當歸傳統歌部,這部分字的聲符和異讀是討論上古歌支關係的抓手。”
二、“埶樂”與“紲袢”通假關係問題
安大簡“是埶樂也”,《毛詩》作“是紲袢也”。
薛培武懷疑:“簡本‘樂’和今本‘袢’爲同義換讀。”呂珍玉提出重點是如何解釋簡本“埶樂”與《毛詩》的“紲袢”的關係。對此孟蓬生認爲:“‘埶樂’和‘紲袢’就是普通的假借關係。”接下來,他列舉了宵元相通的10組例證,並據此認爲:“袢之於樂,猶吅之於龠、管之於龠、管之於籥、雚之於籥、亂之於囂、𡄹之於囂、雚(懽)之於樂、𢍏之於奥也(以上所舉字例大都見於孟躍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音韻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指導教師爲李國英教授)。”
關於宵(藥)元(歌)的音轉關係,孟蓬生提出:“宵(藥)元(歌)二部看似相遠,但從漢代就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種音轉現象。《周禮·考工記序》:‘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鄭注:‘杜子春云:笴,讀爲稾,謂箭稾。’《周禮·考工記·矢人》:‘以其笴厚爲之羽深。’鄭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從近現代來看,最早提出宵歌通轉的是章太炎。章太炎曰:‘交紐轉者云何?答曰:寒、宵雖隔以空界,亦有旁轉。如《大雅》以‘虐謔灌蹻𦽡謔熇藥’爲韻,《說文》訓‘毛’曰‘艸覆蔓’,《廣雅》訓‘蹻’曰‘健’,及夫榦之與稾、㲦之與豪,翰之爲高,乾之爲槀(《周禮》作‘薧’)、瑑之與兆,彖之與逃,讙之與囂,灌之與澆,𡅽之與號,柬選之與撟捎、偃蹇之與夭撟,其訓詁聲音皆相轉也。’其後林義光、龔煌城、馮蒸、梅廣、楊秀芳、張宇衛等先生都曾經有所論述,但從提供的音轉實例上看,基本都沒有超越章氏的範圍,即僅限於同源詞(同源字)和個別韻腳字,幾乎沒有諧聲、異文和假借的證據。拙作《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曾把幽宵侯與歌脂微的通轉關係放在一起討論,拙作《前上古音概論》(《學燈》創刊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曾討論清華簡和郭店簡宵元相通的現象。從近兩年來看,論述最詳、舉證最多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孟躍龍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音韻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指導教師爲李國英教授)。”
11月3日的討論圍繞《桑中》篇展開,主要涉及異文所引出的音韻學論題,如安大簡本“
![]() (
(
![]() )”“
)”“
![]() (
(
![]() )”用作“沬”,“湯”用作“湯”。
)”用作“沬”,“湯”用作“湯”。
一、“坶”
安大簡《桑中》篇“
![]() (
(
![]() )”“
)”“
![]() (
(
![]() )”字,整理者指出該字从坶聲,在之部,是“坶”的繁體。“坶野”即“牧野”,地名。毛詩作“沬”,在微部。“
)”字,整理者指出該字从坶聲,在之部,是“坶”的繁體。“坶野”即“牧野”,地名。毛詩作“沬”,在微部。“
![]() (
(
![]() )”“
)”“
![]() (
(
![]() )”“沬”同是明母字,韻母之、微部音近可通。趙彤說,“坶”即“牧”,有上博簡《容成氏》的例子參照。
)”“沬”同是明母字,韻母之、微部音近可通。趙彤說,“坶”即“牧”,有上博簡《容成氏》的例子參照。
孟蓬生指出,《桑中》篇爲楚方言中的脂(微)、之二部相通提供了新的證據。這與以往的“管夷吾”作“管寺吾”、“匪夷所思”作“匪台所思”、“越公其事”作“越公其次”構成平行的現象。趙彤認爲“管夷吾”作“管寺吾”是韻母方面的語流音變現象,但沒有做進一步解釋。
二、“孟姜”
毛詩“孟姜”,簡本作“
![]() 湯”。
湯”。
孟蓬生認爲“
![]() ”是雙聲符字,《說文》“孟”从子皿聲,而此處“孔”也是聲符。王弘治認爲“乚”是書寫時候的羨筆,還是从“子”。
”是雙聲符字,《說文》“孟”从子皿聲,而此處“孔”也是聲符。王弘治認爲“乚”是書寫時候的羨筆,還是从“子”。
“湯”用作“姜”,張新俊從下文“㚤”“㛚”推測“湯”應該是“婸”,簡本字形有些模糊,故不一定要讀作“姜”。楊軍指出二字疊韻,但聲母有些距離。王志平認爲“湯”“姜”通假並不奇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小口鼎,自名“
![]() 鼎”,對應荊門包山2號墓、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竹簡遣策的“湯鼎”。“康”从“庚”聲,則和“湯”應該能以*kl-形複輔音解釋,經歷*kl->*t-的演變過程。黃旭初、黃鳳春有文章較好地解釋了“昜”“庚”“康”“湯”“漮”的聯繫(黃旭初、黃鳳春《湖北鄖縣新出唐國銅器銘文考釋》,《江漢考古》2003年第1期,9-15頁)。譚樊馬克引潘悟雲的漢語比較材料(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282-286頁)支持王志平的觀點:“第282頁有包擬古爲原始瑤語找到的漢語關係詞:
鼎”,對應荊門包山2號墓、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竹簡遣策的“湯鼎”。“康”从“庚”聲,則和“湯”應該能以*kl-形複輔音解釋,經歷*kl->*t-的演變過程。黃旭初、黃鳳春有文章較好地解釋了“昜”“庚”“康”“湯”“漮”的聯繫(黃旭初、黃鳳春《湖北鄖縣新出唐國銅器銘文考釋》,《江漢考古》2003年第1期,9-15頁)。譚樊馬克引潘悟雲的漢語比較材料(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282-286頁)支持王志平的觀點:“第282頁有包擬古爲原始瑤語找到的漢語關係詞:
![]() 池、湖對應‘塘’,
池、湖對應‘塘’,
![]() 桃對應‘桃’,
桃對應‘桃’,
![]() 腸對應‘腸’,
腸對應‘腸’,
![]() 杵對應‘碓’。這些都是呼應*kl->*t-現象的。”
杵對應‘碓’。這些都是呼應*kl->*t-現象的。”
王弘治認爲“昜”“唐”相通無礙,但是否“昜”“庚”因此相通,還需分析條件。譚樊馬克還指出“唐”从“庚”聲,“唐”的異體“啺”从“昜”聲,且裘錫圭將甲骨文的“
![]() ”讀爲“蕩”,“王心
”讀爲“蕩”,“王心
![]() ”即爲“王心蕩”(裘錫圭《殷墟甲骨文考釋四篇·釋
”即爲“王心蕩”(裘錫圭《殷墟甲骨文考釋四篇·釋
![]()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437-438頁),也是平行例證。“姜”的聲符“羊”和“湯”的聲符“昜”同音,“祥”和“餳”也都是邪母陽部字,構成很好的平行。“姜”與“庚”屬牙音字,“唐”與“啺”屬舌音字,“羊”與“昜”、“祥”與“餳”屬齒音字,都是通轉現象。趙彤有文章談到了“羊”聲的“姜”“祥”等字的諧聲現象(趙彤《以母的上古來源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2005年12月,12-18頁)。
》,《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437-438頁),也是平行例證。“姜”的聲符“羊”和“湯”的聲符“昜”同音,“祥”和“餳”也都是邪母陽部字,構成很好的平行。“姜”與“庚”屬牙音字,“唐”與“啺”屬舌音字,“羊”與“昜”、“祥”與“餳”屬齒音字,都是通轉現象。趙彤有文章談到了“羊”聲的“姜”“祥”等字的諧聲現象(趙彤《以母的上古來源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2005年12月,12-18頁)。
孟蓬生說“孔”“孟”相通和“姜”“湯”相通,就和吳語的“王”“黃”不分類似。楊軍認爲“王”“黃”不分是方言經歷了音變,並不能僅因爲二字疊韻通假就不考慮聲母。孟蓬生回應說上古音也是從前上古音演變過來的,音變存在聲變和韻變以及聲韻皆變三種可能。研究韻母變化時,假定聲母不變;研究聲母變化時假定韻母不變。從韻文總結的韻腳字也只能得出韻部信息,並不是研究者不管聲母。
洪波認爲聲母的變化可能聯繫到上古漢語的形態性詞綴,這一屬性會影響聲音,值得重視。王志平指出“孟姜”是專名,沒有發生語法變化的必要。
執筆:李蓉 譚樊馬克
審覈: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