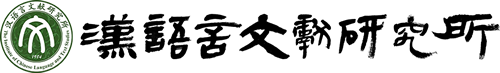附件: 讀書班 _ 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2019.10.31).pdf
讀書班 _ 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2019.10.31).pdf
10月31日主要研讀了《柏舟》一詩,內容涉及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其中音韻學方面關於語氣詞“兮”、“乎”的討論最為激烈。
一、文字學
這一方面主要討論了 “髧彼两髦”中的“髦”字。
王寧(記錄者按:棗莊廣播電視台)提出,《毛詩·鄘風·柏舟》“髧彼两髦”的“髦”字,簡文作“
 ”,整理者隸定作“
”,整理者隸定作“
 ”,疑為“鶩”字異體。右旁徐在國先生認為是“矛”,整理者又疑是“杪”,楚簡中固有“杪”,作“
”,疑為“鶩”字異體。右旁徐在國先生認為是“矛”,整理者又疑是“杪”,楚簡中固有“杪”,作“
 ”,从木眇聲,被假借為“冥”,故該字右旁為“杪”的可能性不大。
”,从木眇聲,被假借為“冥”,故該字右旁為“杪”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大家在討論“兮”和“乎”字的讀音時涉及與兩字相關的“虖”、“平”、“丂”、 “
 (杖?)”來源和演變問題,詳見下文音韻討論部分。
(杖?)”來源和演變問題,詳見下文音韻討論部分。
二、訓詁學
這一方面主要探討了“母可天氏”的釋義問題。
呂珍玉提問:“請問‘母可天氏’怎麼講?”寧鎮疆認為:“‘母可天氏’,猶言娘哎,天呐!《竇娥冤》裡控訴: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作天。只是指訴对象不同而已。”王志平表示,自己曾寫文討論過“只、氏、兮”三字,其中就涉及到“母也天只”,可供參考(記錄者按:《〈詩論〉發微》,《華學》2003年第6輯)。王寧認為,“‘母可天氏’就是母兮(啊)天只,《毛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正義》:‘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后天者,取其韻句耳。”不过,王寧又認為古人將“天”指“父”,實有不妥。
三、音韻學
1、關於楚簡聲系問題
楊軍首先提出:“從安大簡《詩經》看,有部分楚人好像分不了聲母清濁。楊建忠老弟可試試,看看能不能理出一條線索?” 楊建忠對此表示,可將安大簡《詩經》與楚簡聲系結合試一試。
2、關於語氣詞“兮”“乎”
孟蓬生認為:“‘可、氏’與傳世本‘也、只’一樣,是語氣詞。現在的問題是可(也)、氏(只)和兮(可)的用法究竟有沒有區別?”楊建忠認為“兮”中原雅言歸支部,楚方言歸歌部,至於用法方面還要比較。孟蓬生補充說:“它們更早的時候都在魚部。”高永安提出,胡明揚先生曾認為“兮”就是“唦”,湖北人常用。孟蓬生說:“劉釗先生在前面已經指出‘兮’和‘乎’都从‘丂’,‘猗’也从‘丂’,音應該也有關係。”楊軍對此表示:“光看韻是這樣的,但諧聲的時候聲母就不同,還是後來聲母不同了?什麼導致了這些聲母分化的?”孟蓬生進一步分析了‘兮’和‘乎’兩字的音韻變化,並認為“兮”和“乎”所从的應該是“丂(于)”,與“可”的聲符有所不同。上古或前上古時期,魚部的讀音為a,上古後期歌部的讀音為a,所以記載語氣詞的字多從魚部字換作歌部字,其實自然的語音沒有多大變化。上古後期,歌部字和支部字相近,故“兮”字又讀入支部。
楊軍提問說:“在《詩經》時代是否‘兮’類語氣詞只有一個?”孟蓬生認為從人類語言的自然屬性看,“乎、兮、呵”所記的詞大致就是現在的“xa(ha)”。楊軍不贊成此說,他認為語氣詞在方言裡差異是比較大的。孟蓬生回答道:“這要看各方言間真正能夠對應的詞是哪一個。” 楊軍認為:“現代漢語經歷了太大的變化,不說上古(說也說不清楚),就在五胡亂華到隋唐,北方話大抵是胡人講的漢語為主,漢語被胡人接受。”
孟蓬生提出,可以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看看人類語言必有的語氣詞,然後看看上古漢語裡的語氣詞中,哪些能對得上號,哪些對不上號。楊軍表示:“語氣詞有個現象,往往隨前一個音節變音(記錄者按:勞乃宣提出的)。”孟蓬生提供了相關工具書的資料,指出“兮”與“只”字中古音衹有聲調差別,兩字在上古相通應是很自然的。楊軍則認為中古的章組也有可能來自舌頭音。孟蓬生引用李家浩先生的觀點:“ ‘只’和‘也’(注意:跟‘它’字不同)為一字分化。从‘只’得聲的‘伿’,中古音也讀喻四,跟‘也’的聲母相同,而從韻母看,上古時期支歌相通,所以語氣詞‘只’和‘也’相通也是沒有問題的。”薛培武提出,胡敕瑞教授有篇文章,也涉及這個問題。(記錄者按:《試論“兮”與“可”及相關問題(上)》https://www.baidu.com/link?url=Ls2tLRRR68WVQikZHC397KXnP65N11sTLOYXjqQ8_GSd6o2cdo7CUWqPG9gdcVgf&wd=&eqid=afdb83fe0001a8d5000000065dba4f63)孟蓬生補充道:“記憶所及,除了上面志平兄和敕瑞兄的文章。好像張雁(北大教授)多年前在《語文研究》上有一篇討論“兮”字的(記錄者按:《殷墟卜辭“乎”字的構形分析》,《語文研究》2001年第2期),師兄黃易青在北師大學報有一篇討論這幾個字的關係的文章(記錄者按:《上古詩歌語氣助詞“只、些、斯、思、止”的詞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孟蓬生轉貼張雁教授文章(記錄者按:《殷墟卜辭“乎”字的構形分析》,《語文研究》2001年第2期)結論:“兮字從乎字分化而出。乎,匣母魚部;兮,匣母歌部(與‘柯’同部)。可見卜辭時代歌魚二部可以通轉。以流證源,卜辭乎字从丂(柯)得聲,當屬不誣。由于字形幾經變化,乎字從一個形聲字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獨體記號字,造字之初的形符、聲符以及構形理據遂湮沒而不為人知。”因此,孟蓬生說劉釗教授與張雁教授觀點是一致的。
3、關於“虖”字
薛培武提供一則新信息:“之前王森兄發表過一个觀點,認為金文中“呜呼”的“呼”,即‘虖’,構形中所谓的‘乎’,其實都是‘兮’,字从兮从虍聲。‘乎’在早期文字中不存在,‘乎’是从‘虖’分離出来,而保留母字读音的。早期文字中的‘乎’都是‘平’。”劉釗表示:“‘虖’从‘兮’,後變為从‘乎’,我在《構形學》裡就說過,這更說明‘乎’‘兮’相通。”王森補充說:“我的觀點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乎’字,皆當改釋為‘平’。平,使也。在卜辭和金文中,用為使令動詞。”劉釗認為甲骨文“乎”改釋為“平”行不通,字形差太遠。孟蓬生提問王森;“那兩字的構形關係如何解釋?一個三點,一個兩點,他們之間有無關係。”王森回答說:“甲骨文中,所謂‘乎’字,下部所从,不是‘柯’字,也不是‘兮’字的下部,而是和‘昜’字下部相同。我和陳劍老師的觀點相同,這個部件讀為‘杖’。甲骨文所謂‘乎’字,下部不是‘丂’。真正的‘丂’(幽部讀音)到了西周才出現的,就是從‘考’字中分化出來的。”劉釗表示:“从不从‘丂’先不說,字形怎麼解釋呢?”王森認為,“丂”這個部件有不同的來源。董珊插話說:古文字“乎”“息”皆从气,“气”是從“息”截出來的字。孟蓬生總結幾位學者的討論說:“‘丂’字有不同的來源大家應該沒有意見。關鍵是其中哪幾個可以認同,這個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王森進一步論證自己觀點:“我釋‘平’,字形從‘杖’,上面兩點或三點為飾點或者表示塵點等等。平為抨之本字,表示杖擊。抨,使也。平,使也。見古書用例。”劉釗表示自己衹關心甲骨文的“乎”怎麼和後來的“平”字形聯繫起來的。王森答復劉釗:“ 劉老師可以看看《新金文編》,其中的西周“乎”字,和春秋“平”字是無縫銜接。”王森強調自己的觀點是因為“虖”字出現了,“乎”才真正出現。甲骨文所謂“乎”字,下部所从與“昜、甹、寧”諸字相同,他提到:“劉釗老師在書中也談到,甲骨文‘寧’字有直接从‘乎’的。這個‘寧’是直接从‘平’聲的。”劉釗表示,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得證明“乎”晚於“虖”。
李春桃則論證了古文字中 “
 (杖?)”字的演變過程。他指出:“甲骨文中的
(杖?)”字的演變過程。他指出:“甲骨文中的
 ,我在一篇未刊小文中認為並不是‘考’字異體,應該是一個陽部字(學者懷疑形體是杖的初文很有道理),在很多辭例中應該就讀為‘昜’。此形與‘河、何’所從的‘柯’並不相同。過去釋為‘考’,或者懷疑與‘柯’有關,可能並不正確。另外,金文作冊疐簋裡面的
,我在一篇未刊小文中認為並不是‘考’字異體,應該是一個陽部字(學者懷疑形體是杖的初文很有道理),在很多辭例中應該就讀為‘昜’。此形與‘河、何’所從的‘柯’並不相同。過去釋為‘考’,或者懷疑與‘柯’有關,可能並不正確。另外,金文作冊疐簋裡面的
 ,過去或釋‘柯、朽、析’,也有問題,這個字就應改釋為‘楊’。逨鼎铭文中‘楊’字作
,過去或釋‘柯、朽、析’,也有問題,這個字就應改釋為‘楊’。逨鼎铭文中‘楊’字作
 ,可證。”王森表示自己完全贊同李春桃的觀點,當時撰文寫這個問題,就是讀了李春桃老師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的文章。蘇建洲提到,陳劍早在2016年已提及這個問題,2018年到政大纔正式對外宣講(記錄者按:陳劍《以一些例子談談甲骨文字考釋可注意的問題》,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2018年11月16日)。
,可證。”王森表示自己完全贊同李春桃的觀點,當時撰文寫這個問題,就是讀了李春桃老師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的文章。蘇建洲提到,陳劍早在2016年已提及這個問題,2018年到政大纔正式對外宣講(記錄者按:陳劍《以一些例子談談甲骨文字考釋可注意的問題》,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2018年11月16日)。
執筆:鄭 婧
審覈: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