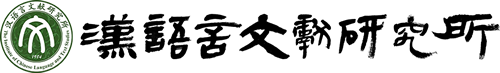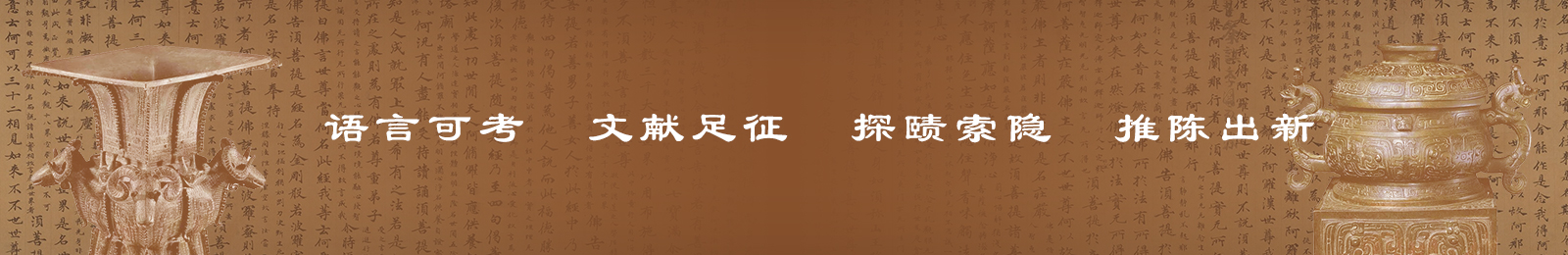附件:讀書班 _ 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 (2019.10.26-10.27).pdf
10月26日研讀《陟岵》,討論內容主要涉及“岵”、“上”兩字的釋義。
一、關於“陟彼岵兮”中的“岵”字
蕭旭列出諸書對“岵”的解釋,《爾雅》:“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岀生也。”《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蕭旭指出:“‘屺’、‘峐’聲轉。《毛傳》與諸書相反,當是誤訓。孔疏已指出《毛傳》傳寫訛誤,王筠、朱駿聲從其說。”
顧國林認為“岵”有可能是現代漢語裡的“崮”。楊軍指出:“語言學第一個基本假設:‘沒有不變的語言。’此假設至今從未發現反例,所以無理由顛覆。現在的山東豈能與漢以前山東等而視之?活語言當然重要,但絕不可以一字一音簡單比附,而是要找始終一致的對應規則。且地名也會隨移民現象發生轉移。”蕭旭表示,“崮”是個俗字,應弄清楚此字的語源,才曉得他是否就是漢以前的“岵”字。高永安認為:“《爾雅》的成書年代還沒有定論。我願意從戰國說。那麼《毛傳》、《說文》應該在後。兩種‘岵’解的不同在有草無草,共同之處在山。”
二、關於“上慎旃哉”中的“上”字
王寧(記錄者按:棗莊廣播電視台)指出,“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正義云:“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行列時也。”王寧提問道:“‘上’簡本作‘尚’,古人的這種解釋是否有問題呢?”楊軍認為這種解釋是典型的增字解經。董珊指出:“‘尚’在西周卜辭中很常見,是表希望的語態。在《左傳》禱詞中也有,沈培先生曾討論過。今本《陟岵》‘上’應是‘尚’字。”
10月27日對10月25日所討論的“權輿”一詞作進一步申說,繼而探討安大簡《詩經·園有桃》中“無(
 )極”的釋義問題和“我”與“言”的異文問題。
)極”的釋義問題和“我”與“言”的異文問題。
一、關於“權輿”
顧國林25日提出:“不知‘權輿’能否讀爲‘元始’,‘始’爲以聲,和‘輿’都是以母型的發音。” 孟蓬生指出:“《大戴禮記·誥志》:‘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其中‘權輿’用作動詞,爲‘萌芽’義,意義較爲抽象。詞義引申從具體到抽象更爲容易,就像‘元始’之‘元’本義爲‘頭’,引申爲‘開始’一樣。‘權輿’從‘萌芽’引申爲‘開始’,跟‘萌’從‘萌芽’義引申爲‘開始’義一樣。我們一般不認爲由‘開始’義引申爲‘萌芽’義(儘管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這是我們不同意直接讀‘權輿’爲‘元始’的主要理由。”顧國林26日提出:“‘慎’(小心謹慎)+動詞是非常自然的用法,‘慎罰’‘慎辭’‘慎守’‘慎用’‘慎察’都是先秦文獻中的用例。”孟蓬生指出:“上古名詞、動詞或其他詞性轉變不一定需要形式標誌,怎麼知道所舉辭例一定是‘慎’加動詞,而不是‘慎’加名詞呢?以‘慎罰’爲例,《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明德’與‘慎罰’並列,難道其中‘罰’不可以理解爲名詞?又以‘慎辭’爲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其中‘辭’難道可以理解爲動詞?”
二、關於“無(
 )極”
)極”
董珊認爲:“《園有桃》之‘士無極’,‘極’應即金文常見卿‘士作四方極’之‘極’,謂四方準臬。君無道,而士無君上可從,無君無父,旁人見士自爲驕縱,乃不知士心之所憂。士唱著憂傷的歌,姑且到四方去散散心,憂思傷心,還是不要多想了。《詩經》之‘無極’與‘四國’,可比對金文‘四方極’。《園有桃》詩中是寫這位士不被了解,被罵爲無良的讀書人。”
呂珍玉指出:“安大簡作‘無極’,毛詩作‘罔極’,《詩經》中出現若干‘罔極’句,如‘士也罔極’‘昊天罔極’。屈萬里《書傭論學集·罔極解》討論《詩經》中成語,以爲‘罔極’是當是固定成語,作‘無良’解釋,乃詈人,或詈天語。另,王國維《觀堂集林·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姜昆武《〈詩經〉成語零釋》都是此類討論。”且補充:“《毛詩》中只見‘罔極’,未見‘無極’,且‘罔極’都釋爲‘無良’。《園有桃》詩中是寫這位士不被了解,被罵爲無良的讀書人。”王寧指出《毛詩》中沒有“無極”,只有‘罔極’,並猜測都是‘無準則’義。“罔極”“無極”可有區別。薛培武則認爲:“‘罔極’‘無極’就是同一個詞。解釋的不同在於‘極’的不同義位及其語境義。‘極’和‘則’雖然都可以訓爲‘則’,但是兩者詞義的來源和內涵不一樣。”孟蓬生提出:“‘無極’有兩義,一個是無準則義,一個是無極限,如‘與天無極’。”並認同薛培武觀點,補充到:“詈詞之‘無極’當由‘無準臬’之義引申而來。”就王寧、呂珍玉推測“無極”“罔極”應有區別的觀點,孟蓬生指出:“後代利用詞形(字形)來區別詞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正如糴和糶一樣,我們不能根據後代的區別說他們最初不是來自一個源頭。”呂珍玉認爲:“莫非爾極,永賜爾極。’‘極’,訓爲則,‘無極’就是‘無準則’,‘無良’由其義引申,當無問題。‘以極反側’,‘極’正也。較難與‘則’等同’。”王弘治認爲:“‘極’可以訓‘則’,但聲母部分未安,如果可以排除‘則’‘極’同現的例子,或許可以用作精組中從喉牙音來的例子。”孟蓬生指出:“既然喉牙音可以通齒音,何來聲母未安之說?即便真是同源詞,連用也不受影響。”
三.關於異文“我”與“言”
王化平指出:“《毛詩》‘我歌且謡’,安大簡作‘言歌且【謡】’。第二章同樣位置是‘翏(聊)行四或(國)’,所以作‘言’字比較合適。這一組異文對理解《詩經》中‘言’字的訓釋應該有幫助。在‘我歌且謡’這句中‘我’表示人稱代詞更合適。”蕭旭認爲:“《詩經》中的‘我’字,不都是第一人稱代詞,也有作虛詞用者,‘我V我V’句式即是。”
執筆:李蓉 鄭婧
審覈: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