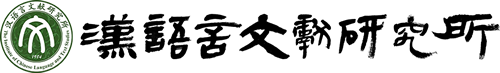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0.6).pdf
讀書班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0.6).pdf
讀書班 | 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10.6)
编者按:“安大简《诗经》读书班”微信群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建立的学术微信群,发起人为孟蓬生、王化平,旨在研讨安大简《诗经》的相关问题,推动跨学科学术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群为纯粹的学术研讨群,崇尚实学,绝去浮言,提倡争鸣,鼓励创新。微信群建立以来,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响应和支持,在群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今起本所网站和公众号将陆续推出读书班讨论纪要,以飨读者,敬请大家关注。
6日的討論涉及到文字學、音韻學和文獻學三个方面的問題。文字學方面,對“豐”、“灘”、“艱”、“難”、“荊”、“創”、“言”、“樛”等字進行了討論。音韻學方面,主要探討了諧聲與合韻問題。文獻學方面,對《詩經》“南有”話語系統的形成,以及《秦風·渭陽》“曰至渭陽”和“至於渭陽”這一對異文的形成原因進行了討論。
一、文字學
(一)關於《樛木》的“豐”字
在9月30日的讀書班中學者們已對此字作了較為集中的討論(記錄者按:詳見《安大簡〈詩經〉讀書班討論紀要(2019.9.30)》,“語言與文獻”公眾號2019年10月6日),趙彤在之前討論的基礎上補充說:“孟老師‘挑食’之喻有理。不過我還是認為必要的淘米、擇菜也不能忽略。所謂‘壴亡亡’(記錄者按:即
![]() )之字,沈培老師和我提出的‘彭’,或許仍可備一說。我原來認為釋‘彭’可能要讀為‘傍’,與毛詩不同,有可疑。現在認為‘彭’讀‘荒’應該也沒問題。”孟蓬生回應說:“謝謝趙兄賜教!咱們雙方都是從音韻反推字形,咱們完全可以提不同的意見,供古文字學界參考、批評(或批判?)”趙彤說:“是的。期待文字學上有更好的解釋。”孟蓬生繼續說道:“‘彭’字據《說文》是彡聲,也是侵部字。所以我前面說過,如果證據充足,連亡聲都可以劃到前上古音的侵談部去。”“‘
)之字,沈培老師和我提出的‘彭’,或許仍可備一說。我原來認為釋‘彭’可能要讀為‘傍’,與毛詩不同,有可疑。現在認為‘彭’讀‘荒’應該也沒問題。”孟蓬生回應說:“謝謝趙兄賜教!咱們雙方都是從音韻反推字形,咱們完全可以提不同的意見,供古文字學界參考、批評(或批判?)”趙彤說:“是的。期待文字學上有更好的解釋。”孟蓬生繼續說道:“‘彭’字據《說文》是彡聲,也是侵部字。所以我前面說過,如果證據充足,連亡聲都可以劃到前上古音的侵談部去。”“‘
![]() ’或體作祊,从方聲。旁从方聲,何琳儀先生認為上从凡聲。是風之訓放,淵源有自。亡聲前上古音可以考慮入收閉口韻。”
’或體作祊,从方聲。旁从方聲,何琳儀先生認為上从凡聲。是風之訓放,淵源有自。亡聲前上古音可以考慮入收閉口韻。”
(二)關於《灘(漢)廣》的“灘”字
“灘”字原作(簡15):

孟蓬生首先提出“‘灘’从難聲怎麼理解”的問題。趙彤說:“‘灘’讀‘漢’已多見。我覺得是清鼻音hn的特殊演變,就如‘咍’是清邊音hl的特殊演變。”楊軍補充說:“清化鼻音是一整套,hl類也可以看成邊擦音。”孟蓬生對“灘”、“漢”可諧的意見表示贊同,同時指出“要想說服別人不容易”。劉洪濤認為:“其實跟‘凥’、‘處’關係一樣,舌音跟舌根音的關係,‘凥’‘處’——‘艱’‘難’。‘創’和‘荊’也是。”並出示了自己的文章以供參考(記錄者按:《〈說文〉“艱”字籀文、‘難’字古文考》,《勵耘語言學刊》2016年第1期,第266—276頁)。劉寶俊說:“‘難’聲字讀‘灘’、讀‘漢’,類似現象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構擬為清鼻音hn-。但可能是音變現象,漢語送氣塞音或塞擦音多有變化為清擦音現象,在今贛方言以及廣東台山四邑方言th-聲母字,多讀h-聲母,羅常培《臨川音系》認為是失去了t而變為h-。苗瑤壯侗語族也有同類音變現象,台灣張光宇(賢豹)似有文章論及。另‘休思’之‘思’,應是原始漢語-s詞尾的遺留。”對此,孟蓬生指出:“‘艱’、‘難’有可能是同源分化(同源字兼同源詞),如何解釋?”劉寶俊解釋說:“‘難’聲字既可讀h-,自可與‘艱’同源。”孟蓬生說:“演變過程假定是這樣:hn——h——k?”封傳兵說:“‘灘’字,《廣韻》有三音:奴案切,水奔流貌。他幹切,水灘也。呼旱切,水濡而幹。對‘灘’諧聲‘難’,又讀曉母和透母,可能有啟發。”孟蓬生則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家實際上是在沒有對諧聲序列進行完整的疏理情況下匆匆忙忙下的結論”。王弘治指出:“清鼻音的構擬比較好解釋‘灘-漢’的問題,‘漢’字在日語中的名付讀音是nara,當屬於早期借詞。”對於這一點,孟蓬生提醒王先生要“根據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把‘難’字完整的諧聲序列疏理出來之後再下結論,為時不晚”。王弘治回應說:“這是很自然的嘛,清鼻音序列一般出現鼻音、擦音和送氣塞音,基本不出現不送氣清塞音。可參李方桂先生說。”孟蓬生強調:“我一直在提倡全息音韻學,首先把目前該吸收的成果儘量吸收,需要古文字學界和音韻學界的共同努力。”王弘治又指出:“從甲骨文看,‘艱’與‘難’所从部首無關,金文中漸生出火字形,乃與暵字本形相混。”孟蓬生則認為“這個恐怕還要聽聽古文字學家怎麼說”。封傳兵繼續補充道:“考察‘難’字的諧聲要追根溯源,最終落實到‘堇’字的諧聲系列,這裡面內容很豐富。類似‘攤’字,也諧聲‘難’字,又音他丹切。”孟蓬生對此表示贊成。楊建忠指出“‘艱’的聲符也有爭論”。楊建忠找到了一批“難”、“艱”諸字的諧聲字,如下圖:
![]()
![]()
![]()
孟蓬生對楊先生出示材料表示感謝,並指出關於“堇”聲和“難”聲的關係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歡迎大家繼續討論。(記錄者按:以上為10月6日的討論內容。)
薛培武認為:“‘堇’和‘難’字聲符來源應該是不同的。早期文字‘堇’是从黑得聲的(‘堇’即‘黑+口’,有些黑的用法就與【黑+口】無別),‘艱’是从堇得聲(說到底也是从‘黑’得聲的一個字)。早期文字還有一個‘黑+口+火’,隸定為‘火+堇’差不多,但是沒法證明是‘熯’,假如說這個字是‘熯’的話,所从的‘堇’也沒說是聲符呀。後來的‘難’所从的東西可能是這個來的,慢慢地與‘堇’混了。……洪濤先生之前也發過文,他講得肯定透徹。”鄭振峰認為:“堇,从土从黃省。”對此,薛培武說:“鄭老師,個人理解,堇从黃形是形體演變的結果,是‘黑’的頭部下移與身體‘大’形重疊的結果(上面有個‘口’形,頭形不好安置,索性結合身體‘大’形,形成一個成體),恐非溯形。甲骨文的形體確實是从黑的。”孟蓬生指出張富海有文討論‘堇’聲和‘難’聲的問題,葉磊旋即指出張富海此文為《說“難”》,發表於《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57-363頁,2015年。(記錄者按:以上為10月7日上午的討論內容。)
(三)關於“荊”“創”的關係及“荊”字的古音歸部
劉洪濤首先提及這個問題,并指出自己會有文章對此集中討論。王志平也提及他有文章對“荊”字有新的討論。孟蓬生則提倡在讀書班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王志平指出:“其實,‘創’、‘荊’一字,馬敘倫和聞一多等已有此說,尤其是聞一多,論述尤詳。拙作衹是對他們的觀點有所補充而已。”劉洪濤說:“李家浩、劉釗、李春桃等都有討論,基本觀點都是把‘荊’歸為耕部,跟陽部通轉。我的主要觀點是楚簡‘刑+田’就是楚文字的‘荊’字,上古音是陽部,所謂‘刑’是从‘井’、‘刅’(創)聲之字之變。‘荊’不以‘刑’為聲,後人誤解,遂誤以‘刑’為聲,遂誤歸耕部。”董珊指出“荊為陽部,似是古文字界的常識”。王志平說:“‘荊’、‘刑’古讀為陽部,是王念孫的觀點。對此,趙曉慶引述頗詳。”董珊認為“‘刑’的語源有待討論”。劉洪濤說:“‘荊’就是‘楚’。我前面提到的先生(記錄者按:指前面提到的李家浩、劉釗、李春桃等先生)都認為耕部。”董珊則指出:“我最初求學時,老師們就說‘荊’是陽部,从‘創’聲,似無異說。”王弘治則指出:“段玉裁把‘荊’歸第十一部,也就是耕部。”對於上述爭議,孟蓬生指出:“大家提供各種不同的材料是很重要的,但我提醒大家,不要用一種材料否認另一種材料,更明確地說,不要因為古文字的材料簡單否定傳世文獻的材料,反之亦然。”王弘治說:“‘荊’、‘創’這種例子,如說字形一致,沒有問題,若說是同一詞源,還需謹慎。字形相同,語義相近,也未必同詞。如‘月’、‘夕’之類,也有此例。”孟蓬生補充道:“所以大家都要去檢視對方的材料是否可信,不然的話就成了自說自話了。”
學者門對“荊”、“創”二字的討論繼續熱烈進行。劉洪濤說:“我的觀點是楚簡‘刑+田’就是楚文字的‘荊’字,上古音是陽部,這些都不是原創,但近來覺得需要補充論述一下。假如我早點明白,就不會把《昭王毀室》的‘(刑+田)落之’讀為‘請落之’。” 董珊說:“‘(刑+田)落之’,我讀為‘釁落之’,心裡還是從文例考慮的。”劉洪濤指出:“其實就是‘荊落之’,用楚國的落禮。”程少軒說:“從古文字字形看,‘荊’从‘刱/創’聲;‘荊’聲符與耕部之‘井’無關;‘荊’本應與‘創’同為陽部字;‘荊’與陽部相通的例子不能作為耕陽相通的證據。這幾層意思,我聽數位師友提過,如大前年聽洪濤兄談過,前些年陳劍老師古文字形體源流課上也講過不止一次,董珊老師前面也說‘荊’屬陽部似為古文字學界通識。但這幾層意思,居然就從來沒有人寫成完整的論文公開發表過。”又說:“《楚居》注釋直接把‘荊’和‘京’聲聯繫,很可能整理者也是默認‘荊’屬陽部的。”劉洪濤說:“這是‘荊’字,楚文字中的‘刑+田’前些年大家似乎還不普遍認為是‘荊’,我主要講這層意思,陽部啊,創聲啊,都是基礎、前提,我自己不懂,所以犯了錯。”楊軍說:“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把‘井’認作聲符,所以是耕部;把‘刅’認作聲符,就成了陽部。文字使用久了,又沒有做過規範,發生這種事也在情理之中。”劉洪濤緊接道:“‘荊’讀耕部就是讀錯了,不是音韻學的問題,是文字學的問題。”又說:“葛信益先生《〈廣韻〉訛奪舉正(增訂稿)》把這種現象總結為‘本無其字,因訛而成字,遂添音切者’,舉有古丸切之‘涫’訛作‘㴦’遂有居戎切的讀音,與專切之‘鉛’訛作‘鈆’遂有職容切的讀音等30餘例。該文原載《音韻學研究》第一輯,第330-359頁,中華書局1984年;後收入氏著《廣韻叢考》,第49-58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又舉“貢”、“贛”的關係進一步證明其說。程少軒又指出:“‘刑’和‘刱’馬王堆帛書裡就訛混了,可能是從楚文字底本轉抄而來的文本,將‘刑’抄成‘刱’,恐怕其中也有音近的影響,或許未必全是文字學層面的問題?”劉洪濤回應說“西周金文就混了”。程少軒繼續說:“帛書的訛混與西周金文的例子不太一樣。金文應該是單純的字形訛混。從戰國文字轉抄而來的字形,把常見的刑德的‘刑’字寫成‘刱’,還是有點怪的。”董珊說:“《昭王毀室》的‘既(刑+田)落之,王入,將落’,‘刑+田’如洪濤兄說,就是‘荊’字,我想或可就讀‘創’,訓為‘始作’,句意謂‘已開始舉行落成典禮,楚王入宮室,將開始做落成祭祀活動。”鑒於大家持續的爭論,孟蓬生說:“建議討論雙方都潛心關注一下前人的相關研究後再做進一步的爭論……雙方提出的一些材料都需要對方再做些檢視和消化,以使我們的討論更上一層樓!”
(四)關於《詩經》中的“言”字
孟蓬生首先提出可以圍繞“言刈”之“言”是否人稱代詞進行討論。蕭旭認為:“《詩經》中動詞前的‘言’字,毛傳:‘言,我也。’劉淇、王引之、朱駿聲、楊樹達等皆認為‘言’是‘不為義’的語助詞。黃侃調和上面二說,在《經傳釋詞》批語云:‘言訓我者,引申以為語詞,猶我本施身自謂,引申以為語詞也。’胡適《詩三百篇‘言’字解》又前進一步,明確指出其用法與意義,解為‘乃’。高亨‘言’讀為‘焉’,解為‘乃’、‘爰’、‘於是’,也用的胡說。我認為動詞前的‘言’字,含有意志作用,表示‘將欲’。《戰國策·燕策一》:‘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作‘今王欲傳之子之’,又‘將傳國子之’。此言訓將、欲之明證。”孟蓬生對此發問道:“安大簡‘言’、‘我’異文的情況兄注意到了嗎?”蕭旭回答道:“安大簡還沒看。那表明毛傳有傳承。”孟蓬生說:“是的。所以有必要重新審視舊結論呀。”蕭旭繼續說:“動詞前的‘於’字,當一起考慮。包括‘曰’、‘欥’、‘聿’等字。”薛培武指出:“梅廣先生那篇《詩三百篇‘言’字新議》,也挺有意思,也可以參考。收在他《上古漢語語法綱要》開篇了。”蕭旭補充說:“《詩經》中動詞前的‘言’字,胡朴安(1924)、諸祖耿(1965)、俞敏(1982)、陳士林(1989)、田樹生、黃樹先(2007)、何蟠飛(臺灣)、王松木(臺灣)及我(1992)都有討論。”呂珍玉說:“《漢廣》‘言刈其楚’‘言’字為第一人稱‘俺’、‘卬’,梅廣《詩三百篇‘言’字新議》論之甚詳,該文分別為‘言’字句解釋,歸納出‘言’字的不同用法,是後出轉精之作。”
(五)關於“喬”和“樛”
孟蓬生首先提出可以圍繞“喬木”和“樛木”的關係進行討論。顧國林說:“‘樛(朻)’即‘喬’,看成用字差異合理,即高大的樹,原因:(1)‘樛(朻)’《詩》裡是高大義,‘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這是拍馬屁語,以喬木大樹喻主人,周邊奴才圍繞。樛即高大。(2)喬的‘高’義,有同源詞支持(見下)。(3)樛(朻)舊釋有‘木下句’、‘兩股相交’不可取,這是受了‘朻’字面的影響,以字貌取義。”
二、音韻學
學者們就諧聲、合韻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
王志平指出:“字的歸韻未必一定是分別部居不雜廁的,合韻通轉都是語音變化的表現。所謂旁轉的音變就是從一部到另一部的母音交替。從陽部到耕部也衹是a到e的一個音變,我們不能說所有的字都是乖孩子,讓呆在家裡就一動都不帶動的。可我們音韻學家都把這些字當成了乖孩子,不許越雷池一步的。”王弘治說:“如從《詩經》用韻看,陽耕相距較遠,幾乎沒有成例。”對此,孟蓬生指出:“諧聲跟用韻都是研究上古音的寶貴資料,就一般原則而言,諧聲時間更早些。《詩經》是否陽耕通押衹能作為旁證,關鍵在於主張該字在陽部的學者提供的證據是否可靠。”王弘治說:“還是舊話,例不十,法不立。”孟蓬生則認為:“這句話也要謹慎!如果現代漢語是例不十,法不立的話,古代漢語尤其是上古漢語和前上古漢語,那一個例子就足夠了。兩位數學比我學得好,根據語言材料的多寡建立一個模型,看看語料和語言樣例的比例應該如何計算?”又說:“我拿中古庚韻的例子來否定上古耕陽分部,兄贊成嗎?”王弘治說:“大前提是,陽耕二部的界限是明確的。所以在使用‘通轉’這個術語時,要明確其內涵,如果確定詞源無誤,則需解釋這種通轉產生的具體原因。認為兩部可通,這是有問題的,那後代分化的原因為何?”孟蓬生說:“您的前提是您的材料、邏輯決定的,大家現在就在努力探討原因呀。”又說:“段玉裁是分開支部和歌部的,是不是可以說明二部的界限是明確的?但段玉裁是否因此就不承認支歌合韻了呢?”王弘治回應說:“所以董同龢即主張歌部再分。”孟蓬生說:“分細了就沒有合韻了?”王志平說:“大家討論通轉,從來都是就具體字例,而不是就韻部的分合。段玉裁合韻之說就是為濟韻部之窮。所謂知其分乃知其合,知其合乃知其分。合韻與分部並不矛盾,是一體二面的問題。”顧國林說:“上古音分時代層次,我是很贊同的。不僅如此,我懷疑諧聲越早,‘音準性’越差,早期諧聲,可能衹是‘大致提示發音’,這種‘大致’到什麼程度,不排除放棄母音的準確,尤其在一些音節較長的字裡。即,諧聲規律衹服從統計上的‘基本準確’,到個例裡,有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例外(甚至韻尾的不同部位,母音的差異等)。原因是,早期漢字音節很長,可用聲符數量又少,總會碰到不理想的選擇。我對待諧聲原則不機械,現象第一位。”對此,孟蓬生說;“建議多接觸古文字資料,不要總停留在懷疑的階段。還有,統計更適合大資料,資料越多越精確,資料越少誤差越大。請兄用統計學分析一下《詩經》裡的脂微合韻。看看您的結論是什麼?”
三、文獻學
(一)關於安大簡真實性問題
針對讀書班外有人質疑安大簡真實性的現象,孟蓬生說:“裘錫圭先生、李學勤先生都相信清華簡是真的,也都相信安大簡是真的,果如有人所說,這兩批簡是假簡,您難道不想瞭解古文字學界和古史學界的頂尖專家是如何被蒙騙的嗎?還有,您看了上面的樣簡,您是否覺得造假者的水準超過了您呢?這些是不是更激起了您閱讀這兩批簡的願望呢?欲求真知,請從讀簡開始!”
(二)關於《詩經》中的“南”及“南有”
孟蓬生首先提出可圍繞“《詩經》裡為什麼總說‘南有’,這種話語傳統是怎樣形成的”這一話題進行討論。顧國林對《詩經》中方位詞出現的次數進行了統計,得出數據為:南72、東54、北22、西17,他解釋說:“大概和作品所處位置有關,周人從西北向東南擴散,前進方向成為興趣點,好比一位往西旅行的人,他的日記裡的西字要多於東字。還有一個原因,是不是古人更喜歡太陽的方向呢?又統計了一下《山海經》:南265、北343、東459、西271。《山海經》是相反的,對北方更感興趣,這大概和它在南方(楚國?)有關。放在今天也成立,北方人的話題裡,‘南’會多一些,南方人的話題裡,‘北’會多一些。大致可以說明,《詩經》的主體部分,是周人的思維和筆觸(包括《國風》),廣大東方殖民地和土著文化,不在《詩經》裡。《國風》應是進入諸國的周人殖民集團(‘王人’)創作的。”劉洪濤也作了一些討論。呂珍玉說:“‘南’應是指南方江漢之地,這些開頭句子,毛傳都標興,個人認為是套句式的興,猶如山有……隰有……,或者揚之水……之類。《詩經》是音樂性文學,疊章複沓,呈現不同曲式,如《樛木》是AAA曲式,起興句‘南有○○’,傳唱在不同地區,會相互影響。即便在同一地區,也不忌諱採用這種套句起興。”
(三)關於《秦風·渭陽》的“曰至渭陽”及其異文
沈培分享了他在簡帛網發表的《試析安大簡〈詩經〉〈秦風·渭陽〉的詩義及其與毛詩本的關係》一文供大家討論。王化平指出:“王先謙說‘曰至渭陽’,魯詩作‘至於渭陽’。但查《四部備要》中《列女傳·秦穆公姬》卻作‘曰至渭陽’,與毛詩無異。王先謙還引《後漢書·馬援傳》,說韓詩與毛詩亦同。所以,如果說毛詩有異,那這個訛誤就是比較早的。”沈培說:“謝謝補充魯詩的異文。估計‘渭陽’的產生就是秦火之後漢人聽記時發生的吧。但正如您所言,魯詩這個異文可能靠不住,所以諸家未取。”王化平說:“就是,魯詩的這個異文有可能是《列女傳》流傳過程中產生的。”沈培說:“很可能。”
執筆:何義軍
審覈:王化平
終審:孟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