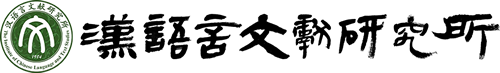內容提要:漢語史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為前上古音的時代,這是毋庸論證的。但長期以來,一些從事上古音研究的學者沒有明確清晰的前上古音的觀念,這導致了一系列消極後果:1.相信《詩》韻,不相信諧聲。2.株守目前的上古音分部不敢越雷池一步。3.偏重歷史比較法而忽視歷史考據法。4.古音學蛻變為古音構擬學。本文對前上古音研究的觀念、材料、方法、研究成果及意義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並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對前上古音系的基本格局(僅限於韻部)作了一些初步推測。
關鍵詞:上古音 前上古音 古韻分部 閉口韻 非閉口韻
二.前上古音的研究材料
舉凡一切可以證明或有助於證明前上古音的東西都可以作為前上古音的研究材料,可以大體分為三大宗:漢語材料、親屬語言材料、非親屬語言材料(對音或譯音材料)。就漢語而言,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大類。傳世先秦文獻(群經諸子)和出土先秦文獻(1.商代甲骨文和金文,2.周代甲骨文和金文,3.春秋金文,4.戰國文字)為主要材料,漢代以後的文獻(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可以作為輔助材料,現代漢語方言也同樣可以作為輔助材料。
(一)漢語材料
1.諧聲系統
上古音研究雖然也要依靠諧聲系統,但實際上是把它當作韻文材料的補充來使用的。王力先生說:“我們認為諧聲偏旁與上古韻部的關係實在是非常密切的。但不是像徐蕆所說的上古的音讀‘本之字之諧聲’,而是相反,字的諧聲偏旁是根據上古的詞的讀音。因此,諧聲偏旁能夠反映古韻部的一些情況,即‘同聲必同部’。但是《詩經》時代離開造字時代已經很遠,語音已經有了發展,當《詩經》與諧聲偏旁發生矛盾時,仍當以《詩經》為標準。”[1]
現在我們研究前上古音,自然應當以諧聲系統為主要材料,而以韻文作為輔助材料。以前人們研究漢字諧聲系統主要是根據《說文》,但《說文》的依據是漢人傳承下來的大篆、小篆以及戰國古文字形,难免存在錯誤。現在我們有幸看到了許慎沒有看到的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資料,使得我們有可能根據這些材料修正《說文》的諧聲系統。今後研究上古音和前上古音所依據的諧聲系統,自然應該是我們根據歷代古文字資料建立起來的諧聲系統,而不是像前人那樣僅僅依靠《說文》的諧聲系統。
在利用諧聲系統研究古音時一定要注意諧聲偏旁的時間層次。理由很簡單,因為漢字不是一天造出來的,而是不同歷史時代逐漸累積的結果。《說文》認為“此”从“之聲”,“斯”从“其聲”,而根據上古韻文或通假資料,此和斯均在支部,與許慎的分析相矛盾。自從段玉裁把之支脂三分之後,就很少有人相信《說文》的分析了。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造字時“此”、“斯”本來跟“之”字在同一個韻部,或者說它們的前上古音都在之部,而到了上古音階段,“此”、“斯”發生音變,跑到了支部。不然的話,“之”、“此”、“斯”都可以作指示代詞用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訿”、“撕”之所以在支部,那完全可能是它們產生時“此”、“斯”已經讀入支部的結果。所以利用諧聲系統研究古音,首先必須把諧聲系統中的時間層次理清或盡量理清,即根據現有材料把每個字形產生的時代弄清楚,儘管這在目前看來還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如果把諧聲系統看作渾淪一團的話,若干年後,人們完全可以根據所謂的漢字諧聲系統,得出現代漢語中還存在著複輔音的荒謬結論。
在利用諧聲系統研究上古音或前上古音時,我們固然不能盲從許慎,但目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輕易否認《說文》對於諧聲的分析,不要因為許慎字形分析的錯誤,拋棄珍貴的聲音信息。例如熊字本从能聲,而《說文》則分析為“炎省聲”。從字形來看,無疑是錯的。但楚文字資料中楚國姓氏熊字,照例寫作“酓”字;現代漢語閩方言中,“熊”字讀“him”。[1]這可以從側面證實許慎時“熊”字收-m尾,至少在方言中如此。結合其他材料,我們完全可以推定“熊”及其所从的“能”前上古音本在侵部。
2.韻文
上古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韻文的“合韻”現象或其他過去被看作例外的現象往往透露了前上古音的信息。
上古音的侵談兩部跟陽部字往往發生膠葛。《詩經·小雅·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談)。秉心宣猶,考慎其相(陽)。維彼不順,自獨俾臧(陽)。自有肺腸(陽),俾民卒狂(陽)。”又《大雅·殷武》:“天命降監(談),下民有嚴(談)。不僭不濫(談),不敢怠遑(陽)。”《急就篇》:“曹富貴、尹李桑(陽),蕭彭祖、屈宗談(談),樊愛君、崔孝讓(陽)。”這些材料提示我們,上古一些陽部字可能來源於前上古的談部。
3.通假字
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的通假字一向是研究者看重的資料(有些人甚至只利用此項資料來做文章),近年出土戰國秦漢文獻中的通假字尤其值得注意。
《詩經·大雅·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漢校官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陽)。”《詩經·邶風·燕燕》:“遠於將之,瞻望弗及。”阜陽漢簡《詩經》作“章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牟有士曰章胥己者。”《呂氏春秋·知度》“章胥己”作“瞻胥己”。《左傳》人名公冉務人,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作[公]襄負人。又《戰國策·楚策四》:“冉子親姻也。”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策》作“襄子親因(姻)也”。《禮記·雜記下》:“四十者待盈坎。”鄭注:“坎或為壙。”《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越人謂鹽曰餘。”《水經·夷水注》:“鹽石即陽石。”
以上這些通假資料表明談部字和陽部字關係密切。結合其他資料(如上文提到的韻文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部分陽部字的前上古音本在談部的結論。[3]
4.同源詞
由於缺少足夠多的韻文資料,同源詞在研究前上古音的地位相應提高。如王力先生認為“在”(之部)和“存”(文部)同源(王力先生《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曾經認為“存”从才聲不可信),我們認為“存”的前上古音有可能在“之(蒸)部”,讀入“文部”是後起的變化。
根據同源詞研究古音本來是中國學者的傳統,章太炎先生論侵幽通轉、談宵通轉,大量使用了同源詞材料。[4]但章黃以後的古音學研究,這個傳統似乎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相對於現當代的中國學者而言,外國學者似乎更看重同源詞資料。如高本漢有《漢語詞族》,[5]沙加爾有《上古漢語詞根》,[6]許思萊有《上古漢語詞源詞典》。[7]個中原因值得中國學者深思。
5.現代方言
根據內部擬測法,我們知道,漢語上古音-n(-t)尾韻中包含了來自前上古音的-m(-p)尾字,但是我們很難把它們離析出來。即便我們知道上古音-n(-t)尾韻合口字中包含了更多的來自前上古音的-m(-p)尾字,我們仍然很難把他們離析出來。根據諧聲偏旁,我們可以離析出來一些。比如,蓋字从盍聲,且都有覆蓋義,我們可以把蓋字的前上古音歸入盍部。但對於那些諧聲系列中所有字都轉移到-n(-t)尾韻的字來說,我們仍然無法把它們離析出來。此時,漢語方言的重要性便得到了凸顯。
例如:我們在上古漢語語料中發現“設”字可以跟“翕”字發生通假關係。《書·盤庚中》:“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我們可以假定,“設”字在上古漢語方言或前上古音中也許是讀-p的,但我們不能排除“設”在上古漢語方言或前上古音讀月部的可能性,因為“翕”字轉入月部之後再跟“設”發生通假關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當我們查閱羅常培先生的《臨川音系》,[8]發現“設”字讀sep,我們原先的假定便因此得到證實。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常常需要綜合運用以上數種資料,使它們之間得到互相印證。可以互相印證的資料越多,結論的可信程度就越高。
研究前上古音的資料跟研究上古音的研究資料相比並不在於種類方面,而在於主次位置的變化。由於我們使用了甲骨文、金文、竹簡等資料,其中韻文的數量較少,相比之下,諧聲、通假、同源上升為主要資料。這對習慣使用韻文來研究上古音並且喜歡用韻文來校訂諧聲的學者們來說,恐怕要經歷一番痛苦的轉變。
(二)親屬語言材料
漢藏語系諸語言存在同源詞。儘管漢藏語系漢語與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相對於印歐語系諸語言的研究而言,其所謂語音對應規律嚴整性稍差而頗為學界垢病。但最近若干年來,漢語與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有了不小的進步,不容忽視。
“熊”字中古音讀匣母,戰國楚系文字記楚國姓氏“熊”寫作“酓”,“酓”中古音在影母,現代閩方言讀him或hom,與中古音相合。藏語“熊”讀“dom”,看上去聲母有點距離。麥耘先生認為“熊(酓——引者補)-能-態”的聲轉關係與 “今(见母)-念(泥母)-贪(透母)”、“堇(群母)-難(泥母)-灘(透母)”的聲轉關係平行,其說可從。[9]其實《說文》以為“熊”从“炎省聲”,也可以看出漢語熊和藏語熊的同源關係。生按,“炎”中古音喻三,上古讀匣紐,“談”从炎聲,中古音讀定母,正跟藏語聲紐相合。
(三)非親屬語言材料
非親屬語言存在關係詞。漢字在歷史上曾為周邊國家借用,漢字在這些國家的音讀對研究漢語語音有很大幫助。比如:如“熊”字,朝鮮語漢字音讀kom, 日語借詞讀kuma。這跟熊字在銅器銘文中寫作“酓”(楚國姓氏),《說文》認為“熊”从炎聲,現代閩語“熊”讀him或hom可以互相印證。[10]現在學者們大都相信“熊”字的前上古音在侵部,跟多宗語言資料可以互相印證有很大的關係。
非親屬語言存在音譯詞。梵語屬印歐語系,漢語屬漢藏語系,但由於佛教的翻譯產生了對音材料。俞敏先生《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是這方面的重要資料。[11]
(本文原刊于《學燈》創刊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4月。此次發表,作者略有修改。)
[1] 王力:《漢語音韻》,《王力文集》第五卷第167、168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
[2] 羅常培:《廈門音系》第58頁、第176頁,科學出版社,1956年;李熙泰:《廈門方言的“熊”字》,《方言》1982年第2期。
[3] 見下文有關“章”字古音的討論。
[4]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始》,《章氏叢書》,浙江圖書舘校刊,1917-1919年。
[5] 張世祿譯為《漢語詞類》,商務印書館,1937年。
[6] 沙加爾著,龔群虎譯:《上古漢語詞根》,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7] Axel Schussler: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8] 羅常培:《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第十七臨川音系》,商務印書館,1940年。
[9] 麥耘:《“熊”字上古音歸侵部補注》,“東方語言學”網。
[10] 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第382、383 頁,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第1-62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