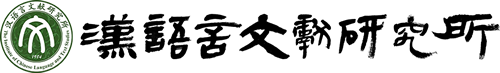摘 要:文章讨论了鼎卦戈上的两个卦象和繇辞,认为第一个卦象当是《周易》卦象,紧随其后的繇辞也出自《周易》,只不过是与通行本不同的某个古本。第二个卦象确实是数字卦,所用筮法和解卦方法可能与清华简《筮法》相同。由于第二个卦象中有五、八这样的“肴”,且出现在上爻和初爻,故占卜结果是不利的。而且在这个卦象中,上为离卦,下为巽卦,两者都是女卦,依《筮法》理论,这也是不利的。基于这两点,第二个卦象后面的占辞自然是“吝”。
关键词:鼎卦戈;数字卦;筮法;周易
本文讨论的鼎卦戈是董珊先生2005年于杭州看到的一件昼锦堂的收藏品,上面的铭文中有数字卦,可转写为鼎卦,故名为“鼎卦戈”。董珊先生对这件器物的形制、年代、真伪作了详尽的分析,可信为两周之际的真品。除此之外,董珊先生还对戈上的铭文作了深入讨论,认为鼎卦戈上的卦形反映的是《连山》或《归藏》之法,与《周易》不同[1]。贾连翔先生也曾讨论过这件鼎卦戈,提出第一个卦例中“六”的写法与第二个卦例明显不同,并认为“第一个卦例并非数字卦例,而是与之同形的代表阴阳爻的卦画图形”,这件器物是“数字卦与单纯卦画并存的例子”[2]。笔者曾两次讨论到鼎卦戈,但只是稍有论及,未曾深入。第一次讨论中推测第一个卦就是《周易》筮法,不过与“大衍筮法”有别,并联系西周陶拍认为第二个卦例中的“八”应有特殊含义,两个卦例是两次起卦的结果[3]。在第二次讨论中,观点稍有变化,认为第一个卦例是“用来查对筮书”的,其后有三条爻辞。第二个卦例是实占记录,所以用数字[4]。梁韦弦先生也曾提及鼎卦戈,认为“其中后者用五、六、一、八写成的易卦当是占筮记录,前者用一、六两个数字或符号写成并附有如卦爻辞者当是来自筮书的写法。”[5]虽然已经有上述讨论,但鼎卦戈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非有深入的专门论述不可说清,有必要专撰一文予以讨论。
一、鼎卦戈铭文中的爻辞
据董珊先生的介绍,“戈铭在戈内正面,其读序自戈内上穿孔下缘起,绕经内后缘,转至内上缘。铭文共22字。”
一六一一一六,曰:鼑(鼎)止(趾)真(颠);鼑(鼎)黄耳,奠止(趾)。
五六一一五八,
 。
。
第二个卦例后的字,董珊先生读作“吝”。这些应该都是确信无疑的,有问题的是“鼑(鼎)黄耳,奠止(趾)”这两句是一条爻辞,还是两条爻辞?为方便讨论,有必要摘引《周易·鼎》的全部卦爻辞:
 鼎:元吉,亨。
鼎:元吉,亨。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关于鼎卦上九爻辞中的“铉”字,廖名春先生曾指出,应是“鼏”字之讹变[6],这是很可信的。“鼏”是指鼎盖,六五爻中有“金铉”,上九中用“鼏”则不与之重复。黄怀信先生则认为六五爻中“金铉”二字衍,上九中的“玉”当做“金”字[7]。鼎之有耳是为便于移动,而铉则是用于移鼎的工具,六五爻由鼎耳而及铉,是有其合理性的。戈铭中“鼑(鼎)止(趾)真(颠)”的语义当与鼎卦初六“鼎颠趾”相同,“鼑(鼎)黄耳”则与六五“鼎黄耳”相当。鼎卦戈上的爻辞与《周易·鼎》虽然相近,但也有几点不同。除了董珊先生指出的语序及“奠止(趾)”之有无不同外,还有一点,即戈铭中并无占断语。而占断语是筮书的必备要素,戈铭中无占断语,当是抄录时省略造成。以此类推,戈铭中可能还省略了“利出否”等句子。
既然戈铭中的爻辞与《周易·鼎》关系很近,则与《归藏》就当无关。湖北王家台秦墓出土有一批易占简,很多学者认为是《归藏》,其中有“鼒”卦,卦形与《周易·鼎》相同,残存繇辞如下:
鼒曰:昔者宋君卜封□,而攴占巫苍,苍占之曰:鼒之

 ,鼒之
,鼒之

 。初有吝,后果述。[12]
。初有吝,后果述。[12]
其中“占之曰”至“初有吝”之间的八个字应当是两条四字句的韵文,像这种句式整齐的韵文在这批易占简中并不少见。而《周易》卦爻辞虽也有押韵,但大多句式参差。辑佚本《归藏》中也有疑似鼎卦的繇辞:“鼎有黄耳,利取
 鲤。”同样是句式整齐的四字句,且前一句极可能取自《周易·鼎》的“鼎黄耳”。无论是辑佚本,还是简本,《归藏》繇辞与鼎卦戈上的繇辞在形式上就有明显差异。
鲤。”同样是句式整齐的四字句,且前一句极可能取自《周易·鼎》的“鼎黄耳”。无论是辑佚本,还是简本,《归藏》繇辞与鼎卦戈上的繇辞在形式上就有明显差异。
以上是从《归藏》方面的材料说明戈铭中的爻辞与《周易》关系更近。以下再解释戈铭既然与《周易》相近,为何又有不同?前文已经说过,《周易》卦爻辞大多有韵。其实,今本《周易·鼎》的爻辞就有韵。初六爻辞中,趾、否、子是之部韵,九二实、即、质是质部韵,九三革、塞、食是职部韵,九四足、餗、渥是屋部韵[9]。至于六五和上九,则是不押韵的[10]。
很显然,如果以“鼎趾颠,利出否”、“颠黄耳,奠趾”成文,则前者是不押韵的,后者虽然有韵,但与象数不合(参看下文讨论)。当然,也有可能本作“鼎颠趾”,戈上作“鼎趾颠”反而是抄写时颠倒了语序。但从语法的角度看,趾是鼎之趾,且鼎趾只能被人颠,因此作“鼎趾颠”更合常用语序,九三“鼎耳革”正是这种语序。作“鼎颠趾”则是出于押韵的需要,在语序上作了调整。同样的,九四之“鼎折足”可能也是如此,早期极可能是写作“鼎足折”的。
换而言之,今本鼎卦的爻辞之所以多数有韵,当是后来修改润色的结果。鼎卦戈的年代是在两周之间,当时流传的《周易》卦爻辞可能未必多数押韵,文本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被人修饰润色,然后才形成基本押韵的情况。关于此点,《左传》有例可为旁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引归妹繇辞云:“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其中“羊”、“衁”、“筐”、“贶”都是阳部韵的字,繇辞是一韵到底的。而在通行本《周易》中,归妹卦上六爻辞作:“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其中“筐”与“羊”协韵,“实”与“血”协韵,虽然同样有韵,但方式上有不同。史苏所引繇辞在意义上并无变化,不过句式整齐,且一韵到底在繇辞中更为多见。通行本上六爻辞采取交韵形式,就同一条爻辞看,全部经文中仅此一例[11]。史苏所引繇辞显然更合经文协韵常例,虽然这条繇辞没有进入通行本,但可以推知的是,通行本的协韵情况是经历过改编的,不会是短期内形成。
总之,铭文中的爻辞虽然与《周易·鼎》有不同,但应当出自《周易》某个古本。确定了这一点,才好辨析“鼑(鼎)黄耳,奠止(趾)”这两句是一条爻辞还是两条爻辞。依《周易·鼎》的爻辞,每一条爻辞都是首先描述鼎的外形或状况。“鼎黄耳金铉”一句是因鼎耳而连及金铉,所要表述的意思并未变化,即鼎便于搬动。若作“鼎黄耳,奠趾”的话,虽然押韵,但“耳”与“趾”一者在上,一者在下;一者用于移动,一者用于稳定,两者的关联度是较弱的。因此,“奠止(趾)”当是另一条爻辞,只不过承前省略了“鼑”字而已。也就是说,戈铭中的爻辞应有三条。而从鼎卦戈的情况看,这三条爻辞极有可能分别对应初爻、二爻和上爻。
由于第一个卦例中的“六”写法特殊,极可能是“符号”,而非数字。因此,第一个卦例及其后面的文字都是从筮书上抄录下来的。第二个卦例与第一个卦例相比,有三条爻是不同的,即初爻、二爻和上爻。之所以抄录这三条爻的爻辞,是因为在将实占记录转写为筮书中的卦象时,字形上产生变化的只有五、八,此其一。另外,清华简《筮法》以五、八、九、四为“肴”,并专章列出四个筮数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说,筮数五、八在筮法中有特殊意义。鼎卦戈抄录五、八所在位置对应的爻辞,当与此有关。
以上推测若不错的话,则两周之际的《周易·鼎》的初爻当是“鼎趾颠”开头,二爻则是“鼎黄耳”开头,上爻则是“鼎奠趾”开头。此种情形与爻象是大体相符的。初爻在最下,所以用“鼎趾”为象,二爻在其上,故此用“鼎黄耳”。上爻则是一卦终了,鼎食已成,所以用“鼎奠趾”为象,并与初爻“鼎趾颠”相呼应。其中“奠”如董珊先生所释,有“定”义。所谓“鼎奠趾”即是鼎足稳定下来,不再移动,寓意君臣分食结束。将这条爻辞放在一卦的最后,也是合适的。
戈铭中的繇辞与今本《周易·鼎》的爻辞之所以有不同,应该是文本流传过程中发生改编的结果。这种改编的目的是为了整齐爻辞,使之更符合象数思维。初爻为足,在最下。二爻“有实”,是为腹,在中间。三爻写耳,在上面。这是一个从下往上的顺序。四爻为足,五爻为耳,上爻为盖,同样大体符合从下往上的顺序。类似的这种改编在咸卦九三、九五中也有,今本的“咸其股”是从古本的“咸其腓”改编而成。咸六二有“咸其腓”,改编者为使九三不与六二重复,且体现从下往上的顺序,故此改“腓”字为“股”字。九五爻帛书作“钦其股”,竹简本作“钦其拇”,今本作“咸其脢”,由于“股”与“拇”、“脢”都无音理上的联系,故此可知今本可能经历过改编[12]。
二、鼎卦戈上的数字卦
前文已经说过,鼎卦戈上的第一个卦象是从筮书上抄下来的,已经是符号卦。第二个卦才能算是数字卦,是记录的实占卦象。在这个实占卦象中,出现了五、六、一、八,共四个筮数。虽然这只是一个卦象,不能为分析其揲蓍法提供足够的数据,但我们知道,若没有二、三、四,则这种筮法的筮数就不能组成一个连续的自然数数列,这是不符合揲蓍法的得数规律的。从张政烺先生开始提出数字卦问题以来,学者就被此问题困扰。2013年,清华简《筮法》的材料逐渐公布,其中将筮数“七”写作“一”形,用四、五、六、七、八、九共六个筮数。借助《筮法》的情况,很多数字卦的筮数终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鼎卦戈上的数字卦中同样有“一”,且没有出现“七”,此点与《筮法》类似。因此,戈上的“一”可能与《筮法》一样,事实上是数字“七”。若是这样的话,则戈上已经出现五、六、七、八这四个筮数,与《筮法》是非常接近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鼎卦戈上的数字卦与《筮法》也是相当接近的。在第二个数字之后有一个被释作“吝”的字,它应该就是占筮最后所得的结果。但我们看第一个卦象后面的三条爻辞,它们的结果都不是“吝”。在《周易》中,初爻的占断辞是“无咎”,五爻的占断辞是“利贞”,上爻的占断辞是“大吉,无不利”。三者相参,断不至于得出“吝”的判断。当然,从目前所知的古本《周易》看,《周易》卦爻辞中的占断辞是有一些异文的。但总体来说,大部分异文并未完全颠覆占断辞的吉凶休咎情势,只是在表述上有些不同而已。因此,可以判断鼎卦戈预测吉凶休咎时并非依据《周易》爻辞,而是另有所据。为寻找这个依据,我们可以引用清华简《筮法》第二十九节中的相关内容(为行文方便,以下用宽式释文):
凡肴象,八为风,为水,为言,为飞鸟,为肿胀,为鱼,为罐筩,在上为醪,下为汏。
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为车,为方,为忧、寡,为瞿。
九象为大兽,为木,为备戒,为首,为足,为蛇,为它,为曲,为玦,为弓、琥、璜。
四之象为地,为圆,为鼓,为珥,为环,为踵,为雪,为露,为霰。
凡肴,如大如小,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燹怪、风雨,日月有食。[13]
在这段讨论“肴象”的文字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其中有五、八,就五来说,虽有日、贵人等比较积极的象征,但较多的是兵、血、忧这类消极的象征。八的象征在吉凶意义上相对含糊。二是最末一部分中,说到“凡肴,如大如小,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燹怪、风雨,日月有食”,总之无一是吉利的。鼎卦戈上的第二个卦象中,初爻是八、二爻是五,上爻也是五,恰好是“作于上”、“作于下”、“上下皆作”。依据《筮法》的理论,第二个卦象只能是不吉利的,戈上写“吝”,是非常合理的判断。
另外,《筮法》分析卦象时常依男卦、女卦,以男女相配者为趋吉,反则可能不吉。鼎卦上离下巽,均为女卦。戈为兵器,为男子或刚强者所操,今遇两女卦,大可说“吝”。事实上,这种依上下卦之男女来判断吉凶的情况,在《周易》中亦有几例。如咸卦艮下兑上,一男一女,故卦辞云:“取女吉。”家人卦离下巽上,皆为女卦,故卦辞说:“利女贞。”因此,从这个角度解释鼎卦戈上的占断辞也是可行的。
上面的讨论证明鼎卦戈上的爻辞出自《周易》,而释卦方法则可能与《筮法》相类。但是,《筮法》与《周易》是完全不同的筮书,鼎卦戈上的卦象和爻辞为什么与两者均有关呢?
在《国语》、《左传》中有三个提及“八”的筮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14]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15]
董因逆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16]
这三个筮例均提到了“八”,显然不同于《左传》《国语》两书中的其他《周易》筮例。其他《周易》筮例都用“某之某”的句式道出起卦结果,分析卦象时则就变爻对应的爻辞或所得卦象之卦辞发论。既是如此,则只关注爻的阴阳属性,不再关注具体筮数。换个角度看,若上述提到“八”的筮例是以静爻为占的话,它们也没有必要说出具体的筮数“八”。无论是以变爻为占,还是以静爻为占,说出爻辞即可,似乎没有必要强调具体筮数。上述三例既然强调“八”,则“八”必然有其特殊意义[17]。不过,本文不想分析这个特殊意义,而是想说这三则筮例都明显与《周易》相关。不仅是卦名见于《周易》,而且都出现了用《周易》卦爻辞解释起卦结果的现象。第一例中,穆姜以随卦卦辞分析自己的命运。第二例中,司空季子用《周易》卦爻辞、卦象支持自己的判断。第三例中,董因引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并分析卦象云“天地配亨”。而且在三例中,有两例出现了相反的判断,即巫史与穆姜、司空季子的意见是全然不同的,同样的矛盾现象也出现在鼎卦戈上:爻辞所反映之吉凶与第二个卦象后的“吝”是相反的。这其实就是在实际卜筮过程,参互使用不同筮法(书)造成的。这种现象当与《周礼》记载的“三易”有关系。
按《周礼》的记载,“三易”均有八经卦,六十四别卦,且均为太卜所掌。至于它们的卦爻辞如何,则没有提及。从这个记载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推测,即当时的“三易”,甚至更多筮法是共享六十四别卦的(卦名的具体写法当然会有一些差别)。而据清华简《筮法》看,春秋战国间可能还有只用八经卦,不用六十四别卦的筮法,其筮书的结构、解卦理论也大不同于《周易》。从一般的卜筮流程看,主要有三个步骤:起卦→解卦→得出结果。起卦涉及蓍草数量、具体揲蓍方法、记录卦象之方法等方面,解卦涉及筮书选择、卦象分析等方面。穆姜和司空季子之所以得出与巫史不同的结论,首先是筮书选择的不同。筮书按一定结构编撰,这个结构与其卦象分析理论相关。比如《周易》有卦辞和爻辞,这是因为在《周易》筮法中,是以卦、爻辞为占断依据的,并有选择爻辞的方法。清华简《筮法》是以典型筮例编撰成书,故此没有爻辞。因此,它的卦象分析方法重在经卦之间的关系、肴的位置等。王家台秦墓易占简没有爻辞,也不见说明具体筮数的象征意义,显然既无法以爻为占,也无法分析筮数的位置等因素,只能据卦象分析吉凶。“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皆八”,都提到了筮数“八”,当然与《筮法》的理论更接近。但是,穆姜、司空季子、董因都不以巫史所用的理论分析卦象,而是据《周易》分析。这就说明,当时诸种筮法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筮书及卦象分析方法的不同。《周礼》的记载、清华简《筮法》都可证明此点。
总之,鼎卦戈上的两个卦象,第一个当是《周易》卦象,第二个则是数字卦象,所得吉凶结论的理据可能与清华简《筮法》类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古人在卜筮过程中,参互使用不同筮书、解卦理论的现象有关。对于职掌占卜的史官来说,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至于在普通贵族和平民间,则可能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
三、鼎卦戈与《筮法》之“四位表”
清华简《筮法》用四个三画卦排成“四位表”的形式,然后分析各位置上三画卦之间的关系,据此关系推断吉凶。由于在《筮法》全篇中,只有八经卦名称,丝毫没有六十四别卦的卦名或相关之概念。因此,李学勤先生在介绍《筮法》时便说:“所有的数字卦,都是并行的两组六画卦,也可看做四个三画卦。”“然而完全不出现六画卦即别卦的卦名,也不用任何卦爻辞……”[18]其后许多学者遂认为《筮法》无六爻卦,如程浩先生认为:“我们之所以说《筮法》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占筮系统,是由于它不用六十四卦以及其独特的命解体系。”[19]林忠军先生认为:“清华简虽然有六位数字组成的卦,却只有三位数字卦占,而无六位数字占。”[20]而李尚信先生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清华简《筮法》虽然是以四位卦的关系来断吉凶,但四位卦有上下之分,上下卦合起来看就是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而不同于无上下卦之分的三爻卦或三位数字卦,所有六爻卦合起来看就是六十四卦。”[21]事实上,李尚信先生与诸位学者的分歧在于对六爻卦或六十四卦之概念的理解。从清华简《筮法》看,上下卦合起来虽然是“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的形式,但它并不据此判断吉凶。在《筮法》的体系中,“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的形式并无实际意义。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六十四卦”。不过,从形式上看,《筮法》又是存在“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的,所以李学勤先生说“所有的数字卦,都是并行的两组六画卦”。
与《筮法》不同的是,鼎卦戈上的第二个卦象很显然是“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它对卦象的分析或是依据《筮法》的理论,这说明《筮法》的“四位表”极可能是早期“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的一种复杂形式,是稍晚时期才发展出来的。“四位表”中当然暗含了“六爻卦或六位数字卦”的形式,至于其中是否有“六十四卦”,则似应另当别论[22]。
虽然鼎卦戈可以说明“四位表”这种形式有其原初的简单形式,但在数字卦中,这并非唯一的一种数字卜筮形式。扶风齐家村H90:79卜骨就很能说明此点。这块卜骨上的刻辞包含数字卦和命辞[23]:
翌日甲寅其商甶瘳
八七五六八七
其祷甶有瘳
八六七六八八
我既商祷甶有
八七六八六七
这块卜骨最大的意义在于,前两个数字卦的吉凶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可由后文有“我既商祷”分析,前两个卦肯定是“吉”的,否则不会举行“商”和“祷”。第一个卦若按阴为偶,阳为奇的规则转换的话,应是上兑下震。兑为少女,震为长男,此卦象正是一男一女,可说是吉利的。若依《周易》,则可参看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结果是相同的。第二个卦上震下坤,坤是女卦,震是男卦,卦象是吉利的。依《周易》的话,为豫卦,卦辞为:“利建侯行师。”同样可说是吉利的。第三个卦象的吉凶不好推测,但从卦象看的话,上坎下震,是两男卦,在《周易》是屯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大体也是不错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三个卦象中都出现了“八”,且频率并不低。在前两个卦象中,“八”共出现了五次,在第一个卦象中不仅有“八”,还有“五”。依《筮法》理论,第二个卦象很难说是吉利的,因为“八”在上、下卦中都有。再者,卜骨上数字“七”的写法也与《筮法》不同。因此,卜骨上的数字卦显然与《筮法》不同,也与鼎卦戈上的数字卦不同。
关于这块卜骨还有另一个被人忽略的地方。上面的第二个卦象是豫,第三个卦象是屯,此与上引《国语》所记重耳筮之而遇“贞屯悔豫,皆八也”极其相近。所谓“皆八也”,当然包含了屯卦。虽然如何解释“皆八也”的含义存在争议,但现在大体可判断“八”应当是指阴爻。因此,不管怎么理解,从重耳的这个筮例看,阴爻“八”是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且可能是消极的。而在H90:79这块卜骨上,第二个卦纵有三个“八”,却仍是吉利的。这就说明,这三个数字卦都不顾及数字“八”的特殊含义的。
以上讨论都是基于揲蓍法的。而揲蓍法所产生筮数的数量多是偶数个,可以说是“成对”出现的。以清华简《筮法》来说,筮数有四、五、六、七、八、九,共6个,四和九,五和八,六和七各自“成对”。在“大衍筮法”中,筮数有六、七、八、九,其中六和九,七和八各自“成对”。如果H90:79这块卜骨上的数字卦也是揲蓍法产生的话,也应符合这个规律。再进一步说,既然不顾及数字“八”的特殊含义,则就不会顾及“五”和“七”的特殊含义,甚至所有筮数的特殊含义都不顾及,即筮数不会有清华简《筮法》第二十九节那样的特殊含义。
从现有材料看,或许可以将H90:79卜骨上数字卦所用筮法追溯到殷商晚期。肖楠先生曾讨论过一块卜甲,上面有三个数字卦,其中一个附有占辞:
七七六七六六 贞吉
此卦若转写成《周易》卦象的话,应是艮下巽上的渐卦,其卦辞是:“女归吉,利贞。”说“女归吉”,是因为巽为女卦,艮为男卦。肖楠先生对此块卜甲的钻凿形态、文字大小、“贞”字写法作了详细分析,推断时代当在殷末周初[24]。此卜甲是在小屯南地发现的,依据上面的刻辞将数字卦所用筮法上推到殷商时期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数字卦中只出现了筮数七、六,七的写法是一横一竖,与常见数字七的写法并无区别。同片卜甲上还有另两个数字卦,分别刻在右甲桥的右上和右下:六七一六七九、六七八九六八,这两个数字卦有筮数一、六、七、八、九,与系有占辞的数字卦或许是同一筮法,也或许不是。
从以上材料看,至少从殷商晚期开始,已经出现一种六爻卦的筮法,这种筮法在分析卦象时,将六爻卦分为上、下两个三爻(画)卦,然后依据两个三爻卦之间的关系推断吉凶。这种方法与鼎卦戈所用筮法不同,但从其分析上、下两卦的关系看,二者又是存在一些联系的。
总之,西周时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六爻卦筮法,两者都要分析上、下两个三爻卦的卦象,不同的地方是,一种要兼顾具体筮数(或“肴”)的特殊含义,一种则可能完全不考虑具体筮数的特殊含义。前一种方法在产生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后者,鼎卦戈第二个数字卦象用的是前一种筮法,清华简《筮法》是用前一种筮法的复杂形式,出现时间可能较晚。
本文原载:《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论丛》,科学出版社,2017年。
注 释:
[1]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贾连翔:《数字卦的名称概念与数字卦中的易学思维》,《管子学刊》2016年第1期。
[3]王化平、周燕:《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63页。
[4]王化平:《由数字卦看〈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张涛:《周易文化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23页。
[5]梁韦弦:《出土易学文献与先秦秦汉易学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6]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要〉校释五则》,《〈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亦收入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1-346页。
[7]黄怀信:《周易本经汇校新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8]释文据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英)艾兰、邢文:《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49页。
[9]杨端志:《周易古经韵考韵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0]黄玉顺认为六五之“鼎黄耳金铉”与上九“鼎玉铉”押韵,参看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11]杨端志:《周易古经韵考韵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2] 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1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20页。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64-966页。
[15]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342页。
[16]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3-345页。
[17]关于这三个筮例与清华简《筮法》的关系,已有多位学者论及。参见程浩:《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刘震:《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筮例的比较研究》,《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
[18]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
[19]程浩:《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20]林忠军:《清华简〈筮法〉筮占法探微》,《周易研究》2014年第2期。
[21]李尚信:《清华简〈筮法〉筮例并非实占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2]笔者认为“六爻卦”与“六十四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应有区别。我们可以将凡是用六个筮数组成卦象的形式都称为“六爻卦”,而“六十四卦”则应指由八经卦两两重叠后形成的六十四个别卦,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有六十四个卦名。而“六爻卦”则未必有卦名,它们可以仅依据上、下两个经卦的关系,以及其中出现的特殊筮数判断吉凶。在这种情况下,“六爻卦”未必会生发出“六十四卦”。详论可以参见王化平、周燕:《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第203-204页;王化平:《由数字卦材料看〈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张涛:《周易文化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刘光胜:《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的转进》,《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23]相关研究文章有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45页;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34-242页;蔡运章:《周原新获甲骨卜筮文字略论》,《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29-39页;张俊成:《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刻辞补释》,《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24]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块卜甲是周人在商朝卜筮的遗物,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03-209页。
作者简介:

王化平,1976年生,湖南隆回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周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