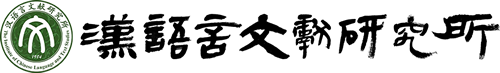注釋及參考文獻: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商代金文的全面整理與研究及資料庫建設”(項目編號16CYY031)、復旦大學“雙一流”建設人文社科一流創新團隊項目“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子課題“商周金文拾遺——《集成》、《銘圖》、《銘續》未錄金文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IDH3148004/005)的資助。[1]http://www.microfotos.com/?p=home_imgv2&picid=2565720。[2]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302-306頁。[3]沇兒鎛(《集成》00203)“龢
 (會)百姓”之“
(會)百姓”之“
 (會)”用法與之相同。[4]金文中一般隸作“倗”的字,本文皆徑作“朋”。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2頁。[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6]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李守奎:《楚大師辥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辥慎編鎛補釋》,《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21-27頁。[8]器銘“子”字,《集粹》釋文筆誤作“士”。[9]參看徐寶貴:《金文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5期。[10]《說文》認爲“剌”字从“束”,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此說有誤。于省吾先生認爲“剌”左旁與甲骨文中的“
(會)”用法與之相同。[4]金文中一般隸作“倗”的字,本文皆徑作“朋”。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2頁。[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6]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李守奎:《楚大師辥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辥慎編鎛補釋》,《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21-27頁。[8]器銘“子”字,《集粹》釋文筆誤作“士”。[9]參看徐寶貴:《金文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5期。[10]《說文》認爲“剌”字从“束”,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此說有誤。于省吾先生認爲“剌”左旁與甲骨文中的“
 ”爲一字(于省吾:《釋
”爲一字(于省吾:《釋
 》,《雙劍誃殷契駢枝》,藝文印書館,1975年,第23-30頁)。裘錫圭先生進一步認爲“
》,《雙劍誃殷契駢枝》,藝文印書館,1975年,第23-30頁)。裘錫圭先生進一步認爲“
 ”是“
”是“
 ”的初文(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0頁。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11]張天恩:《論畢伯鼎銘文的有關問題》, 《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10頁。[12]諸家之說可參看白於藍《金文校讀三則》,《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13]楚大師鄧乂慎編鐘(《銘圖》15511-15518)“萬年毋改”之語可合觀。[14]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年。[15]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16]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7]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18]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9]研究者或認為團山M1就是剌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參看馮峰:《鄭莊公之孫器新析——兼談襄陽團山M1的墓主》,《江漢考古》2014年第3期。
”的初文(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0頁。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11]張天恩:《論畢伯鼎銘文的有關問題》, 《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10頁。[12]諸家之說可參看白於藍《金文校讀三則》,《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13]楚大師鄧乂慎編鐘(《銘圖》15511-15518)“萬年毋改”之語可合觀。[14]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年。[15]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16]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7]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18]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6-170頁。[19]研究者或認為團山M1就是剌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參看馮峰:《鄭莊公之孫器新析——兼談襄陽團山M1的墓主》,《江漢考古》2014年第3期。

圖1


圖2,蓋銘照片及拓本


圖3,器銘照片及拓本
(圖1-3轉引自《集粹》第302-306頁)
補 記:
拙文曾署名謝雨田,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24,2016年1月13日)。此次發表稍作改動,主要觀點未變。拙文在網站發佈後,黃錦前先生亦在同一網站發表《鄭人金文兩種讀釋》一文(2016年1月14日),又2016年9月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卷第278頁)0517號亦著錄了封子楚簠銘文,釋文與拙文基本相同,讀者可參看。
(本文原載:《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輯,如引用請據原文。)
作者簡介

謝明文,湖南邵陽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