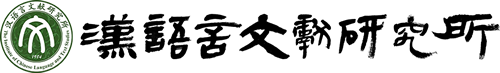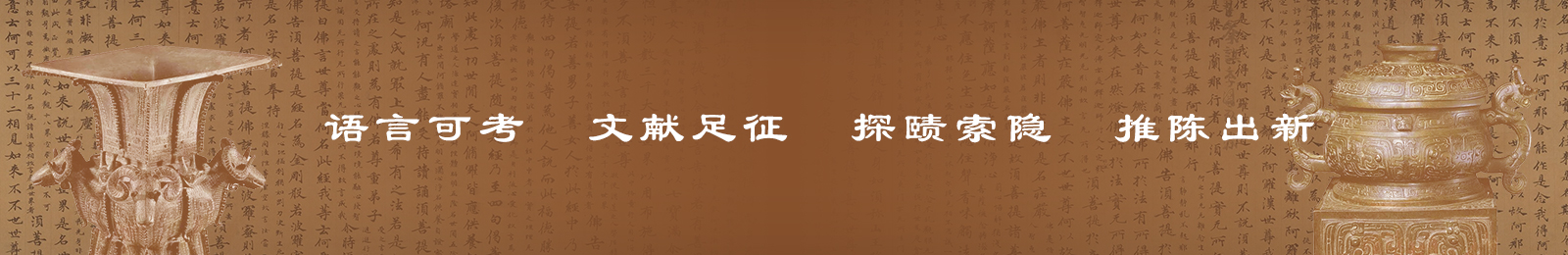大徐本《說文》云:
![]() ,分解也。从刀、
,分解也。从刀、
![]() 聲。(《說文.四下.刀部》)
聲。(《說文.四下.刀部》)
![]() ,
,
![]() 骨之殘也。从半冎。(《四下.歺部》)
骨之殘也。从半冎。(《四下.歺部》)
![]() ,水流
,水流
![]()
![]() 也。从川、
也。从川、
![]() 省聲。(《十一下.川部》)。
省聲。(《十一下.川部》)。
徐鉉等注:「
![]() 字从此,疑誤,當从
字从此,疑誤,當从
![]() 省。」段注云:「大徐曰:『
省。」段注云:「大徐曰:『
![]() 字從
字從
![]() 。』此疑誤。當是从
。』此疑誤。當是从
![]() 省。小徐本作
省。小徐本作
![]() 省聲。良薛切。十五部。」小徐本作「从川、
省聲。良薛切。十五部。」小徐本作「从川、
![]() 省聲。」前人由於資料的限制,故認為「
省聲。」前人由於資料的限制,故認為「
![]() 」從「歺」省或「歺」省聲。但依照目前的認識,「歺」與「
」從「歺」省或「歺」省聲。但依照目前的認識,「歺」與「
![]() 」本是不同的字,其上部有二筆與三筆的不同。陳劍先生指出西周晚期的晉侯蘇鐘有「淖列」重文,「列」字作
」本是不同的字,其上部有二筆與三筆的不同。陳劍先生指出西周晚期的晉侯蘇鐘有「淖列」重文,「列」字作
![]() (《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輯第七頁圖一〇),其左半上端从三曲筆形。[1]何景成先生也有相似的意見,指出西周晚期晉侯蘇鐘「淖淖列列」的「列」字左上從「川」形,與「死」作
(《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輯第七頁圖一〇),其左半上端从三曲筆形。[1]何景成先生也有相似的意見,指出西周晚期晉侯蘇鐘「淖淖列列」的「列」字左上從「川」形,與「死」作
![]() (《新收》0871)寫法不同,《說文》小篆的寫法亦反映出相同的現象。[2]二說皆可從。《說文》「
(《新收》0871)寫法不同,《說文》小篆的寫法亦反映出相同的現象。[2]二說皆可從。《說文》「
![]() 」的寫法與西周晚期〈晉侯蘇鐘〉的「列」字作
」的寫法與西周晚期〈晉侯蘇鐘〉的「列」字作
![]() 一脈相承,往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
一脈相承,往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
 」字。卜辭有如下文例:
」字。卜辭有如下文例:
(1)癸亥卜,貞:旬。三月。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
 風,己明啓。(《合集》21016)
風,己明啓。(《合集》21016)
(2)[癸□卜,貞]:一卜,旬。……
 風……□采雨……六日戊……(《合集》20959)
風……□采雨……六日戊……(《合集》20959)
蔣玉斌先生指出「
 風」與「
風」與「
 風」當讀為「烈風」。
風」當讀為「烈風」。
 與
與
 是《說文》的「
是《說文》的「
![]() 」字,即「列」、「烈」之所從,此說已是學界共識。[3]
」字,即「列」、「烈」之所從,此說已是學界共識。[3]
楚文字也有﹛列﹜。一種是以《說文》「銳」字籀文「
![]() 」爲「列」,[4]如《上博三.周易》簡49
」爲「列」,[4]如《上博三.周易》簡49
![]() 對應今本「列」字;簡45
對應今本「列」字;簡45
![]() 對應今本「冽」。另一種是筆者所指出的,見於《清華六‧子儀》簡12作「
對應今本「冽」。另一種是筆者所指出的,見於《清華六‧子儀》簡12作「
 」。[5]後來《清華七‧越公其事》簡33有「亓(其)見又(有)
」。[5]後來《清華七‧越公其事》簡33有「亓(其)見又(有)
![]() (列)、又(有)司及王
(列)、又(有)司及王
![]() (左)右」一句,石小力先生指出:
(左)右」一句,石小力先生指出:
「
![]() 」字原形作
」字原形作
![]() ,整理者讀為「察」。今按,該字又見於《清華陸·子儀》簡12,作
,整理者讀為「察」。今按,該字又見於《清華陸·子儀》簡12,作
 ,蘇建洲先生釋為「列」(原注:蘇建洲:《〈清華陸〉文字補釋》,簡帛網,2016年4月20日。),該字從戈從𡿪,古文字刀旁與戈旁作為偏旁常通用,如割字從刀,在楚文字中又從戈作「
,蘇建洲先生釋為「列」(原注:蘇建洲:《〈清華陸〉文字補釋》,簡帛網,2016年4月20日。),該字從戈從𡿪,古文字刀旁與戈旁作為偏旁常通用,如割字從刀,在楚文字中又從戈作「
![]() 」,故該字應即「列」之異體。有列,指在朝堂上有位次的大臣。[6]
」,故該字應即「列」之異體。有列,指在朝堂上有位次的大臣。[6]
其說可從。最近剛出版的《清華九‧禱辭》18有「列」字作
![]() ,正從「刀/刃」旁,證明左旁就是「
,正從「刀/刃」旁,證明左旁就是「
![]() 」的寫法,「
」的寫法,「
 」是將「刀」替換為「戈」,釋為「列」沒有問題。此外,《上博九‧陳公治兵》簡11「五人於伍,十人於行。行
」是將「刀」替換為「戈」,釋為「列」沒有問題。此外,《上博九‧陳公治兵》簡11「五人於伍,十人於行。行
![]() 不成,卒率卒命從灋。」的
不成,卒率卒命從灋。」的
![]() ,單育辰先生釋為「列」。[7]由文意來看,其說可從,字形可能是
,單育辰先生釋為「列」。[7]由文意來看,其說可從,字形可能是
 一類寫法的譌變。
一類寫法的譌變。
至於「歺」,當如裘錫圭先生所指出本象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8]甲骨文「
 」(《合集》37387),蔣玉斌先生分析為雙手持「歺」(象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形,即「
」(《合集》37387),蔣玉斌先生分析為雙手持「歺」(象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形,即「
![]() 」字異體。[9]此外,甲骨文有寫作從「歺」、下或從「井」或從「凵」之字,如
」字異體。[9]此外,甲骨文有寫作從「歺」、下或從「井」或從「凵」之字,如
![]() (
(
![]() )(《合集》961)、
)(《合集》961)、
![]() (《屯南》2408),王子楊先生釋為「阱」。[10]「阱」所從的「歺」旁,其上部象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寫法正可對應楚簡的「歺」旁(詳下)。西周金文寫作「
(《屯南》2408),王子楊先生釋為「阱」。[10]「阱」所從的「歺」旁,其上部象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寫法正可對應楚簡的「歺」旁(詳下)。西周金文寫作「
![]() 」(師同鼎「
」(師同鼎「
![]() /
/
![]() 」偏旁),[11]這種寫法可進一步演變為「濬」作「
」偏旁),[11]這種寫法可進一步演變為「濬」作「
![]() 」的上部(詳下),這些寫法都是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的合理寫法變化。但在「
」的上部(詳下),這些寫法都是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的合理寫法變化。但在「
![]() 」(「列」所從)則不會有這些寫法。
」(「列」所從)則不會有這些寫法。
無名組、何組甲骨卜辭中有一個用作田獵地名的「
![]() 」字做如下形體:
」字做如下形體:
(1)
![]() (《合集》—29327)
(《合集》—29327)
![]() (《合集》29328)
(《合集》29328)
(2)
![]() (《合集》29324)
(《合集》29324)
![]() (《合集》28151)
(《合集》28151)
(1)形從「貝」,「
![]() 」聲,(2)形將「
」聲,(2)形將「
![]() 」省為「歺」。裘錫圭先生指出後世「睿」、「
」省為「歺」。裘錫圭先生指出後世「睿」、「
![]() 」諸字中的「
」諸字中的「
![]() 」殆即由上舉甲骨文「
」殆即由上舉甲骨文「
![]() 」所從的「
」所從的「
 」而來。[12]鄔可晶先生詳細考證指出「睿」、「
」而來。[12]鄔可晶先生詳細考證指出「睿」、「
![]() 」實從「
」實從「
![]() 」聲,「
」聲,「
![]() 」字象手(「又」)持鏟臿之類的工具(「歺」)疏鑿阬谷、溝壑(「
」字象手(「又」)持鏟臿之類的工具(「歺」)疏鑿阬谷、溝壑(「
 」),當是疏濬之「濬」的表意初文,同時也可以讀為「壑」的音。[13]其說可從。底下將古文字從「
」),當是疏濬之「濬」的表意初文,同時也可以讀為「壑」的音。[13]其說可從。底下將古文字從「
![]() /
/
![]() 」旁的字形,依照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形體展示如下:[14]
」旁的字形,依照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形體展示如下:[14]
A1.
![]() (豳公盨,《新收》1607)字
(豳公盨,《新收》1607)字
![]() (秦公鎛,《集成》270.1).
(秦公鎛,《集成》270.1).
![]() (中山王鼎,《集成》2840)
(中山王鼎,《集成》2840)
![]() (新蔡葛陵楚簡乙一13)
(新蔡葛陵楚簡乙一13)
![]() (《上博(三)·周易》54)
(《上博(三)·周易》54)
![]() (《上博(三)·周易》54)
(《上博(三)·周易》54)
![]() (《清華二‧繫年》82)
(《清華二‧繫年》82)
![]() (《清華四‧別卦》8)
(《清華四‧別卦》8)
A2.
![]() (《銘圖續》530
(《銘圖續》530
![]() 子煩豆)[15]
子煩豆)[15]
![]()
![]() (《郭店‧性自命出》31)
(《郭店‧性自命出》31)
![]() (《上博(六)·用曰》18)
(《上博(六)·用曰》18)
![]() (《清華五‧湯處於湯丘》19)
(《清華五‧湯處於湯丘》19)
A3.
![]() (楚帛書甲6·76)
(楚帛書甲6·76)
![]() (包山簡183)
(包山簡183)
![]() (包山簡167)
(包山簡167)
![]() (《上博(二)·容成氏》簡38)
(《上博(二)·容成氏》簡38)
![]() (《上博(三)·周易》簡28)
(《上博(三)·周易》簡28)
![]()
![]() (《清華五‧湯在啻門》13)
(《清華五‧湯在啻門》13)
A4.
 (《上博四‧采風曲目》3)
(《上博四‧采風曲目》3)
![]() (《清華一‧金縢》9)
(《清華一‧金縢》9)
![]() (《清華一‧金縢》14)
(《清華一‧金縢》14)
![]() (《清華六‧太伯甲》5)
(《清華六‧太伯甲》5)
![]() (《清華六‧太伯乙》5)
(《清華六‧太伯乙》5)
![]() (安大簡《詩經》5)
(安大簡《詩經》5)
![]() (安大簡《詩經》16)
(安大簡《詩經》16)
![]() (安大簡《詩經》17)
(安大簡《詩經》17)
A5.
![]()
![]() (《上博(一)‧性情論》19)
(《上博(一)‧性情論》19)
![]()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4)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4)
![]() (《上博九‧邦人不稱》3)
(《上博九‧邦人不稱》3)
這些「
![]() 」旁或省「又」為「
」旁或省「又」為「
![]() 」;或省「
」;或省「
 」為「
」為「
![]() 」;或再省為「歺」。A1形是「歺」旁上部常見寫法,也見於上舉甲骨文。A2、A3則是進一步演變,古文字常見。[16] A4形體可比對上舉
」;或再省為「歺」。A1形是「歺」旁上部常見寫法,也見於上舉甲骨文。A2、A3則是進一步演變,古文字常見。[16] A4形體可比對上舉
![]() 、
、
![]() 。A5的演變稍微複雜一點。將
。A5的演變稍微複雜一點。將
![]() 的「歺」旁短橫筆貫穿豎筆,即為「
的「歺」旁短橫筆貫穿豎筆,即為「
![]() 」(「
」(「
![]() 」偏旁),將貫穿的橫筆寫成「U」形,並在豎筆上端左側增添一短筆即為「
」偏旁),將貫穿的橫筆寫成「U」形,並在豎筆上端左側增添一短筆即為「
![]() 」(「
」(「
![]() 」偏旁)。《越公其事》簡51「王乃
」偏旁)。《越公其事》簡51「王乃
![]()
![]() (使)人情(請)
(使)人情(請)
![]() (問)羣大臣及
(問)羣大臣及
![]() (邊)
(邊)
![]() (縣)成(城)市之多兵、亡(無)兵者」,其中「縣」寫作
(縣)成(城)市之多兵、亡(無)兵者」,其中「縣」寫作
![]() 較為特別。整理者注釋指出:「
較為特別。整理者注釋指出:「
![]() ,簡文所從『
,簡文所從『
![]() 』旁與楚文字『達』所從相同,當係訛書。前異文作『
』旁與楚文字『達』所從相同,當係訛書。前異文作『
![]() 』、『還』、『
』、『還』、『
![]() 』,讀為『縣』。」[17]其說可從,
』,讀為『縣』。」[17]其說可從,
![]() 顯然是(
顯然是(
![]() 「
「
![]() (怨)」偏旁,《孔子詩論》03)的錯字。由「
(怨)」偏旁,《孔子詩論》03)的錯字。由「
![]() 」而「
」而「
![]() 」,猶如由「
」,猶如由「
![]() 」而「
」而「
![]() 」。又如楚簡「史/使」作
」。又如楚簡「史/使」作
![]() (《清華九‧治政之道》30),也作
(《清華九‧治政之道》30),也作
![]() (《清華九‧禱辭》05)、
(《清華九‧禱辭》05)、
![]() (《清華九‧禱辭》15)亦可比擬。其次,李家浩先生曾經指出:「戰國文字有在豎畫的頂端左側加一斜畫的情況」,如「陳」作
(《清華九‧禱辭》15)亦可比擬。其次,李家浩先生曾經指出:「戰國文字有在豎畫的頂端左側加一斜畫的情況」,如「陳」作
![]() (《璽彙》1450),亦作
(《璽彙》1450),亦作
![]() (《璽彙》1455)、「匋」作
(《璽彙》1455)、「匋」作
![]() (麓伯簋),亦作
(麓伯簋),亦作
![]() (《古陶文字徵》頁187)等等。[18]又如「殺」可作
(《古陶文字徵》頁187)等等。[18]又如「殺」可作
![]() (《簡大王》07)同簡又作
(《簡大王》07)同簡又作
![]() 。因此在「
。因此在「
![]() 」豎畫的頂端左側加一斜畫即為「
」豎畫的頂端左側加一斜畫即為「
![]() 」。以前筆者也曾舉過「祗」字為例,蔡侯申盤作
」。以前筆者也曾舉過「祗」字為例,蔡侯申盤作
![]() 、《三體石經‧君奭》作
、《三體石經‧君奭》作
![]() ,而在《郭店‧老子乙》12中則作
,而在《郭店‧老子乙》12中則作
![]() 。[19]總之,由「
。[19]總之,由「
![]() 」→「
」→「
![]() 」→「
」→「
![]() 」實為正常演變。 這裡再補充一些秦漢文字的資料。[20]請看「列」(A)與「死」(B)字的寫法:
」實為正常演變。 這裡再補充一些秦漢文字的資料。[20]請看「列」(A)與「死」(B)字的寫法:
(A1)
![]()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68)、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68)、
![]() 、
、
![]() 、
、
![]() (《銀雀山(二)》1543、1714)[21] 、
(《銀雀山(二)》1543、1714)[21] 、
![]() (《張家山.二年律令》28)、
(《張家山.二年律令》28)、
![]() (《張家山.二年律令》260)[22] 、
(《張家山.二年律令》260)[22] 、
![]() (《嶽麓(三)》65)[23]
(《嶽麓(三)》65)[23]
(A2)
 (《馬王堆.經法》12上)、
(《馬王堆.經法》12上)、
 (《馬王堆.經法》49下)
(《馬王堆.經法》49下)
(B1)
![]() (《睡虎地.為吏之道》51壹)[24] 、
(《睡虎地.為吏之道》51壹)[24] 、
![]() (《銀雀山(二)》1858)、
(《銀雀山(二)》1858)、
![]() (《北大秦簡.魯久次》4-148)
(《北大秦簡.魯久次》4-148)
(B2)
![]() (《銀雀山(二)》1833)、
(《銀雀山(二)》1833)、
![]() (《北大漢簡(二).老子》34)
(《北大漢簡(二).老子》34)
將(A1)、(B1)的「
 」筆畫拉直,就會變成(A2)、(B2)的橫筆寫法,這在西漢古隸比較常見,也可以看出(A2)橫筆之上的短直筆是既有的筆畫,而非可有可無的飾筆。《張家山.二年律令》簡28「同列」,即爵位相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注釋指出:
」筆畫拉直,就會變成(A2)、(B2)的橫筆寫法,這在西漢古隸比較常見,也可以看出(A2)橫筆之上的短直筆是既有的筆畫,而非可有可無的飾筆。《張家山.二年律令》簡28「同列」,即爵位相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注釋指出:
該(案:「列」)字圖版作
![]() ,左部從「
,左部從「
![]() 」,於「夕」上有三點,與二六○號簡列(
」,於「夕」上有三點,與二六○號簡列(
![]() )字同。死字左部從「歺」,於「夕」上作兩點,如一一一號簡死(
)字同。死字左部從「歺」,於「夕」上作兩點,如一一一號簡死(
![]() )字。[25]
)字。[25]
已將「死」從「歺」;「列」從「
![]() 」的不同指出來了。陳劍先生進一步指出:「西漢古隸左邊『歹』旁橫畫上有短豎或其他筆劃者,即使右旁與一般『死』字右旁同,也仍應釋『列』。」[26] 這更說明「
」的不同指出來了。陳劍先生進一步指出:「西漢古隸左邊『歹』旁橫畫上有短豎或其他筆劃者,即使右旁與一般『死』字右旁同,也仍應釋『列』。」[26] 這更說明「
![]() 」上從三筆不是偶然的。馬王堆帛書《九主》20/371「佐主之明,並
」上從三筆不是偶然的。馬王堆帛書《九主》20/371「佐主之明,並
![]() (列)百官之職者也」,其中「
(列)百官之職者也」,其中「
![]() 」寫作
」寫作
 也是明證。有些出土文獻整理者未注意到這個現象,便易將「列」誤釋為「死」。如《北大短漢簡二.老子》第二章簡7「其致之也,天毋己精將恐列(裂)」。整理者釋文作「天毋(無)巳(已)精(清)將恐死〈列〉」,注釋云:「『死』,應為『列』之誤,帛乙作『蓮』,當如傳世本讀為『裂』。」[27]謹案:該字形作
也是明證。有些出土文獻整理者未注意到這個現象,便易將「列」誤釋為「死」。如《北大短漢簡二.老子》第二章簡7「其致之也,天毋己精將恐列(裂)」。整理者釋文作「天毋(無)巳(已)精(清)將恐死〈列〉」,注釋云:「『死』,應為『列』之誤,帛乙作『蓮』,當如傳世本讀為『裂』。」[27]謹案:該字形作
![]() ,顯然就是「列」字。又如《北大漢簡三.儒家說叢》簡5「我欲長有國,欲使死〈列〉都得」,[28]整理者釋為「死」字作
,顯然就是「列」字。又如《北大漢簡三.儒家說叢》簡5「我欲長有國,欲使死〈列〉都得」,[28]整理者釋為「死」字作
 ,看得出來在橫筆之上尚有清楚的短直筆,可見此字本來就是「列」,只是「刀」誤寫為「人」形。也可以反過來說,因為有「短直筆」的制約,雖然形體寫得類似「死」,但在秦漢人眼中是認定為「列」的。又簡7「君慧(惠)[29]臣忠,則死〈列〉都得」,所謂「死」字作
,看得出來在橫筆之上尚有清楚的短直筆,可見此字本來就是「列」,只是「刀」誤寫為「人」形。也可以反過來說,因為有「短直筆」的制約,雖然形體寫得類似「死」,但在秦漢人眼中是認定為「列」的。又簡7「君慧(惠)[29]臣忠,則死〈列〉都得」,所謂「死」字作
 ,橫筆之上似乎亦有短筆,應該也是「列」字。《北大漢簡四.妄稽》簡55整理者釋文作「蚤(早)死之」的「死」作
,橫筆之上似乎亦有短筆,應該也是「列」字。《北大漢簡四.妄稽》簡55整理者釋文作「蚤(早)死之」的「死」作
 ,[30]此字顯然也應該是「列」,簡文讀為「蚤列(裂)之」,正好與上一句「
,[30]此字顯然也應該是「列」,簡文讀為「蚤列(裂)之」,正好與上一句「
![]() 躗之」的「躗」同押月部。大概到東漢的碑文如北海相景君銘、劉熊碑、史晨後碑等將「
躗之」的「躗」同押月部。大概到東漢的碑文如北海相景君銘、劉熊碑、史晨後碑等將「
![]() 」寫作「列」,[31]「
」寫作「列」,[31]「
![]() 」隸變為「歹」,「
」隸變為「歹」,「
![]() 」與「歺」才混而不分。
」與「歺」才混而不分。
以上將「
![]() 」與「歺」的問題交代完之後,現在來看2010年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村(M6096:34)出土的「
」與「歺」的問題交代完之後,現在來看2010年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村(M6096:34)出土的「
![]() 鼎」,整理者將器主名字隸定作「
鼎」,整理者將器主名字隸定作「
![]() 」,沒做解釋。[32]根據上面的討論,此字顯然就是「列」,是將
」,沒做解釋。[32]根據上面的討論,此字顯然就是「列」,是將
![]() 的「刀」旁寫在下面,器主名當釋為「列」。
的「刀」旁寫在下面,器主名當釋為「列」。
附記1:昨晚看到馬超先生在「安大簡詩經讀書班」公眾號所貼出「山西翼城大河口M6069出土金文介紹」一文,於是在公眾號下貼出回覆指出字就是「列」。不久之後接到張新俊先生的來信,張先生說:「前兩天看到文物雜誌上的圖片,鄙見也認為,此字當是列字。」(20200414)與拙說不謀而合。又今日早上論文完成之際,孟蓬生先生告訴我,馬超先生博士後出站報告《近出商周金文字詞集注與釋譯》第14页也將此字釋為「列」。
附記2:本文的主體內容取自拙文:〈「趨同」還是「立異」?以安大簡《詩經》「是刈是濩」為討論的對象〉,中國出土資料學會2019年度第二回大會演講,東京大學本鄉校區20191207。
注释:
[1]參見拙文:〈《上博楚簡(五)》考釋二則〉後所附陳劍先生的意見,簡帛網,2006年12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475。
[2]何景成:〈説「列」〉,《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總第十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頁123-128。
[3]蔣玉斌:〈釋甲骨文「烈風」——兼説「
![]() 」形來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87-92。
」形來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87-92。
[4]參陳劍:〈試說甲骨文的「殺」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0月),頁14。
[5]拙文:〈試論「禼」字源流及其相關問題〉,《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4月),頁545-573、拙文:〈《清華六》文字補釋〉,簡帛網,2016年4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26。後以〈《清華六》零釋〉為題,刊載於《中國文字》新43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7年3月),頁29-30。[6]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2017年4月23日,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html。
[7]單育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雜識〉,發表於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主辦,「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2014年08月27-29日)。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49-66。
[8]參看裘錫圭:〈
![]() 公盨銘文考釋〉,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9注14。另外,鄔可晶、謝明文先生對從「歺」的相關字形有深入的探討,讀者可以參看。見鄔可晶:〈說金文「
公盨銘文考釋〉,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49注14。另外,鄔可晶、謝明文先生對從「歺」的相關字形有深入的探討,讀者可以參看。見鄔可晶:〈說金文「
![]() 」及相關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16-235、謝明文:〈釋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出土陶文字「
」及相關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16-235、謝明文:〈釋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出土陶文字「
![]() 」字——兼說古文字中的「
」字——兼說古文字中的「
![]() 」字〉,發表於上海師範大學主辦,「羅君惕先生《說文解字探原》出版暨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2014年10月)。謹案:「歺」象「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與《說文》「
」字〉,發表於上海師範大學主辦,「羅君惕先生《說文解字探原》出版暨語言文字學術研討會」論文(2014年10月)。謹案:「歺」象「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與《說文》「
![]() 」字下云「歺,殘地阬坎意也」以及《說文》:「
」字下云「歺,殘地阬坎意也」以及《說文》:「
![]() ,殘穿」有關。不過,從「歺」的字更多與「死亡」的概念有關,如甲骨文「葬」作
,殘穿」有關。不過,從「歺」的字更多與「死亡」的概念有關,如甲骨文「葬」作
![]() (《屯》4514),黃天樹先生分析為「象死人之殘骨而有『爿』(『牀』的初文)薦之」(參氏著:《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283)。又卜辭「乙未卜
(《屯》4514),黃天樹先生分析為「象死人之殘骨而有『爿』(『牀』的初文)薦之」(參氏著:《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283)。又卜辭「乙未卜
![]() 贞:旧
贞:旧
![]()
![]() (左)驶(?),其
(左)驶(?),其
![]() ,不歺。」周忠兵先生認為「花東卜辭中常卜馬不死,如《花東》60『自賈馬其有死。子曰其有死。』,此處『不歺』可能也與『死』字意近。」(參氏著:周忠兵〈甲骨文中幾個從「丄(牡)」字的考辨〉,《中國文字研究》第七輯 2006,頁142注4)。其他還有「殂」、「歿」、「歿」、「死」、「殊」、「殮」等等,即《說文》云:「
,不歺。」周忠兵先生認為「花東卜辭中常卜馬不死,如《花東》60『自賈馬其有死。子曰其有死。』,此處『不歺』可能也與『死』字意近。」(參氏著:周忠兵〈甲骨文中幾個從「丄(牡)」字的考辨〉,《中國文字研究》第七輯 2006,頁142注4)。其他還有「殂」、「歿」、「歿」、「死」、「殊」、「殮」等等,即《說文》云:「
![]() ,
,
![]() 骨之殘也」。兩者的詞義是引申關係?或是另有來源?還有待研究。
骨之殘也」。兩者的詞義是引申關係?或是另有來源?還有待研究。
[9]蔣玉斌:〈釋甲骨文中有關車馬的幾個字詞〉,《中國書法》2015年10期,頁139。
[10]王子楊:《釋甲骨文中的「阱」字》《文史》2017年第2期,頁5-15。
[11]同上,頁13。
[12]裘錫圭:〈讀《小屯南地甲骨》〉,《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六卷,頁34。
[13]鄔可晶:〈說金文「
![]() 」及相關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16-235。
」及相關之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16-235。
[14]底下字形取自鄔可晶:〈說金文「
![]() 」及相關之字〉、拙文:《〈郭店〉、〈上博(二)〉考釋五則》,《中國文字》新廿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12月),頁221-225、〈《金縢》「穫」字考釋〉,《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頁351-352。
」及相關之字〉、拙文:《〈郭店〉、〈上博(二)〉考釋五則》,《中國文字》新廿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12月),頁221-225、〈《金縢》「穫」字考釋〉,《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頁351-352。
[15]石小力:〈《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釋文校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6.11.06,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1106193606520128251/20161106193606520128251_.html。
[16]這種演變過程請參見拙文:《〈郭店〉、〈上博(二)〉考釋五則》,《中國文字》新廿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12月,頁221-225、拙文:〈《金縢》「穫」字考釋〉,《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頁351-352。
[17]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中西書局2017年,下冊第140頁。
[18]李家浩:〈傳遽鷹節銘文考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二〉,《海上論叢》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頁24。
[19]參見拙文:《〈郭店〉、〈上博(二)〉考釋五則》,《中國文字》。
[20]底下內容參見拙文:〈北大簡《老子》字詞補正與相關問題討論〉,《中國文字》新41期,2015年,頁97-100。又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15年9月2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13。
[21]參見楊安:《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續)》(2013.07.31首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old/srcshow.asp?src_id=2088,頁76。
[22]鄭介弦:《《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文字編》(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蘇建洲教授指導),頁377。
[23]朱曼寧:《《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文字編》(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蘇建洲教授指導),卷四,頁122。
[24] 秦簡的「歺」旁多寫作「
![]() 」,參見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13-114、朱曼寧:《《嶽麓書院藏秦簡(參)》文字編》,卷四,頁118-119「死」字條。
」,參見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13-114、朱曼寧:《《嶽麓書院藏秦簡(參)》文字編》,卷四,頁118-119「死」字條。
[25]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01注六。
[26]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四冊,《老子》甲本,頁9注14。
[27]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24注3。
[28]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下冊,頁211。
[29]「慧」讀為「惠」,見抱小:〈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11.17,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645。
[30]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圖版頁11,釋文頁70。
[31]清.顧藹吉編撰:《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75。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上冊,頁537-538。
[32]謝堯亭、王金平、楊及耘、李永敏、張王俊:〈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6096發掘簡報〉,《文物》2020年1期,頁7、12。